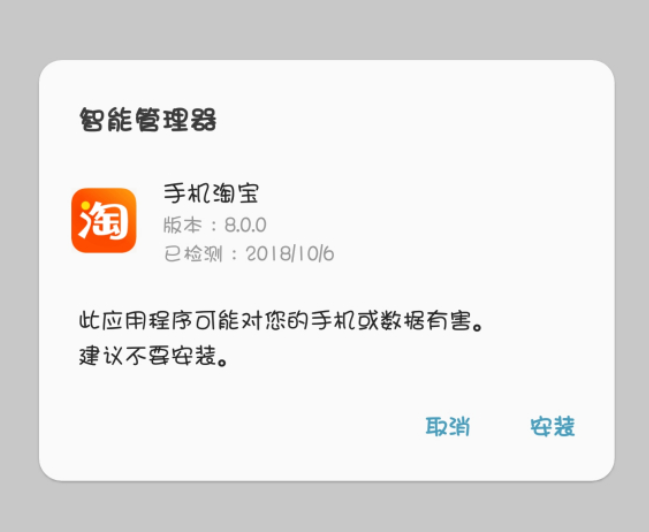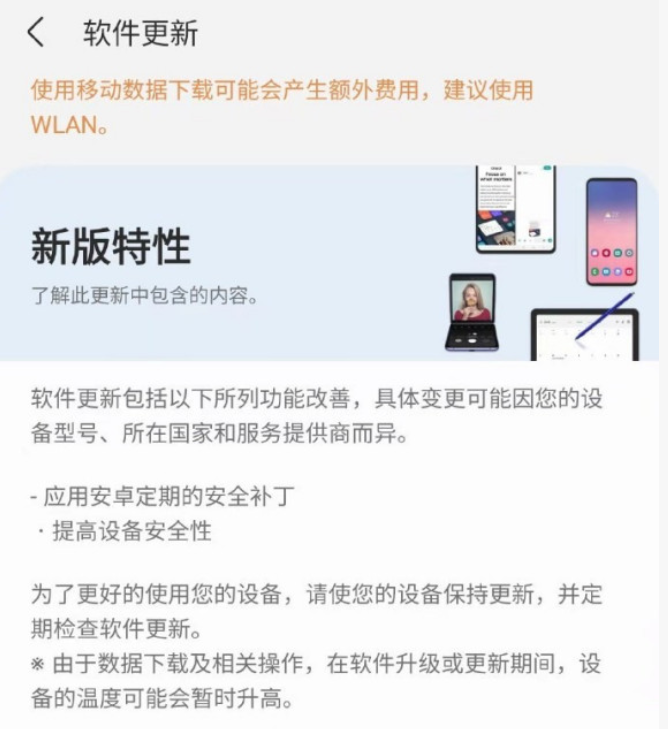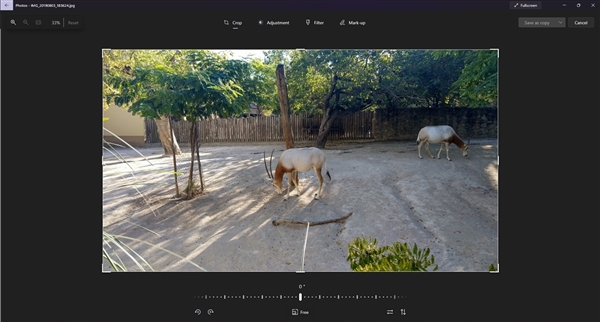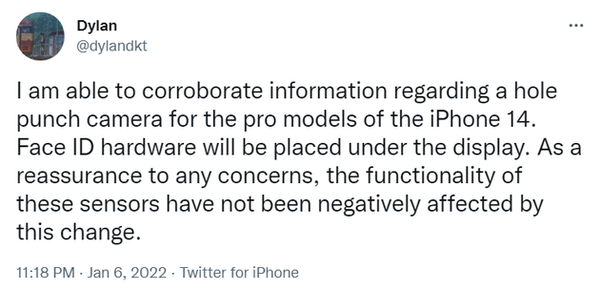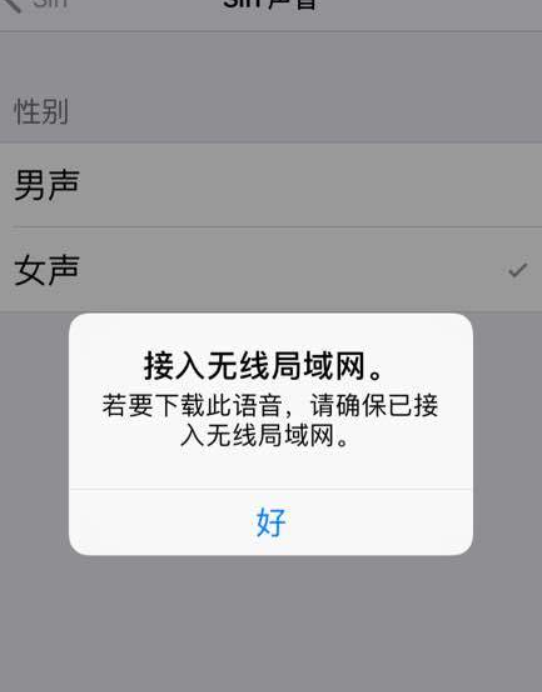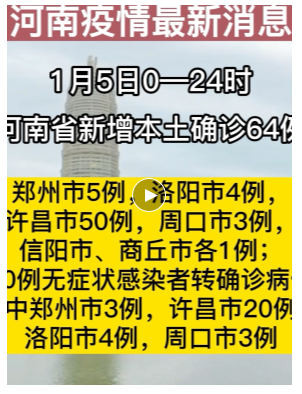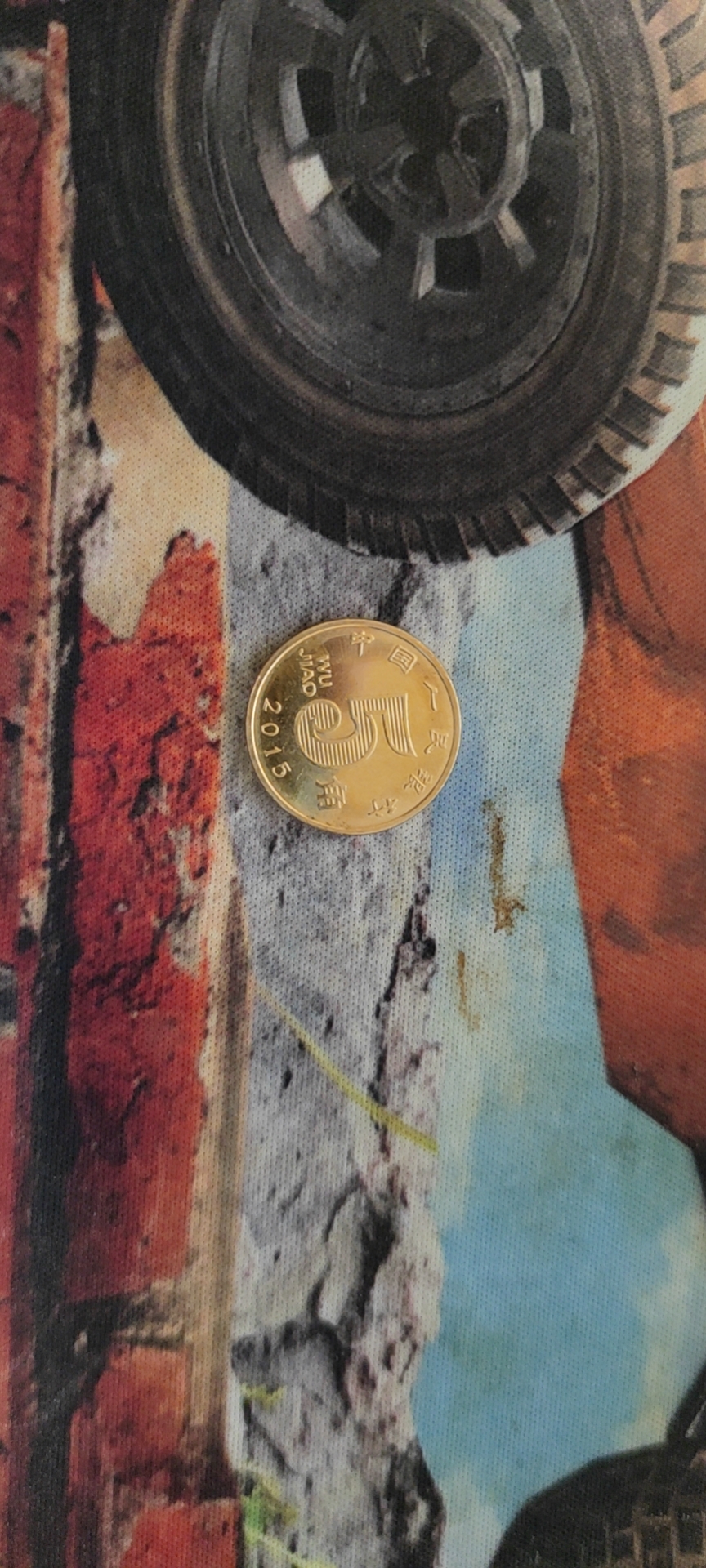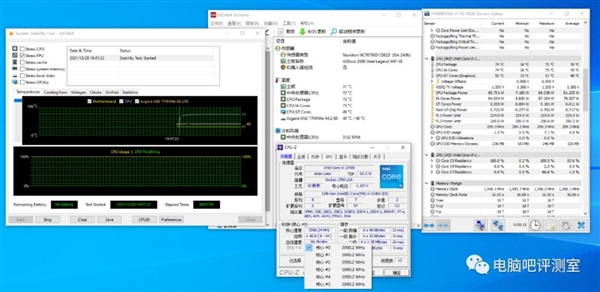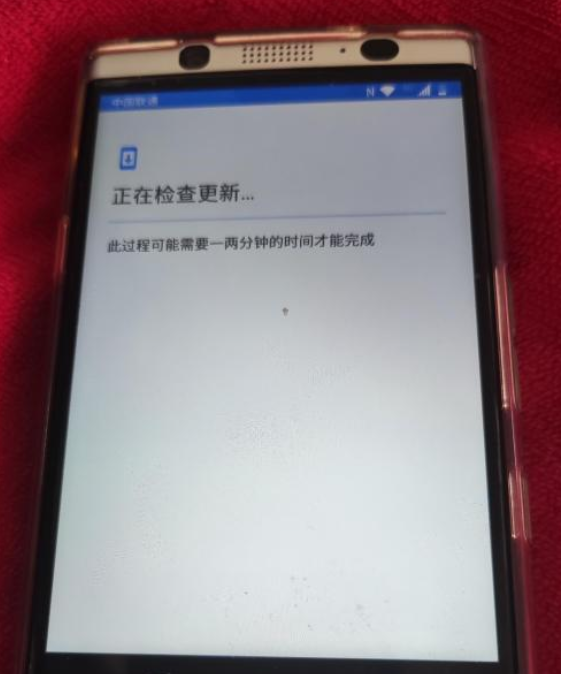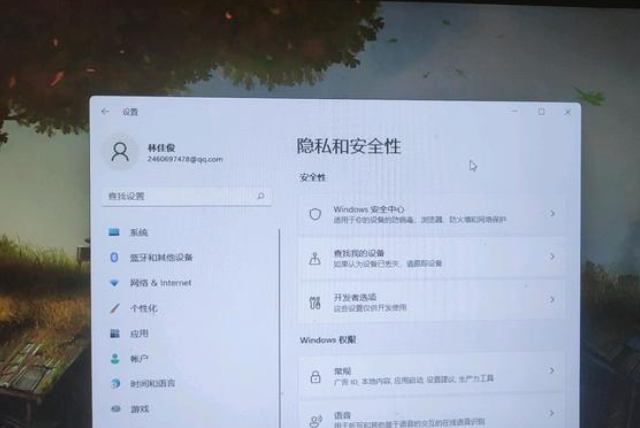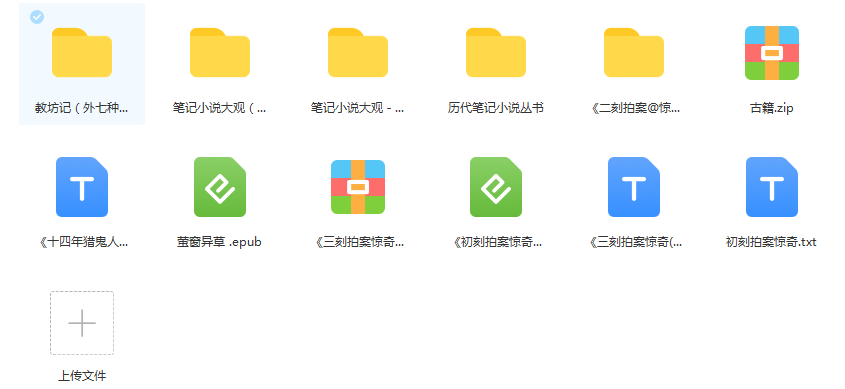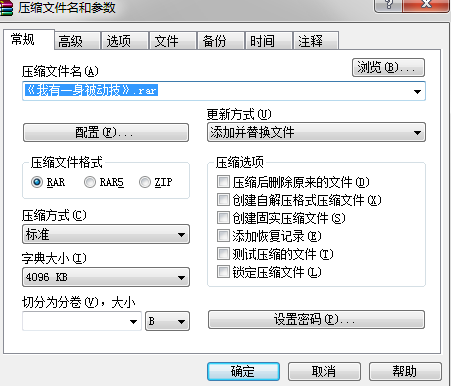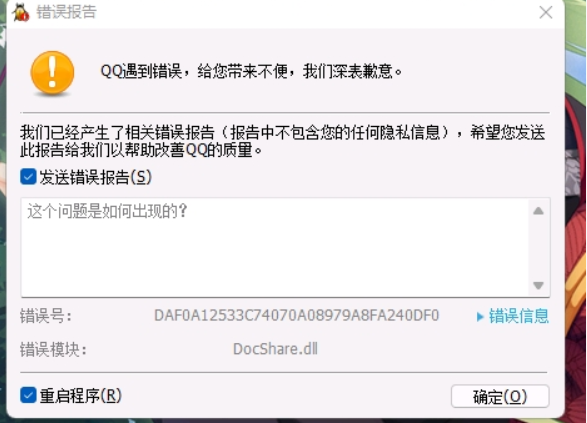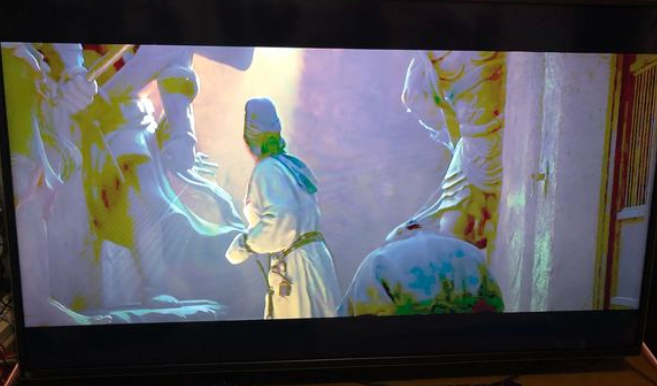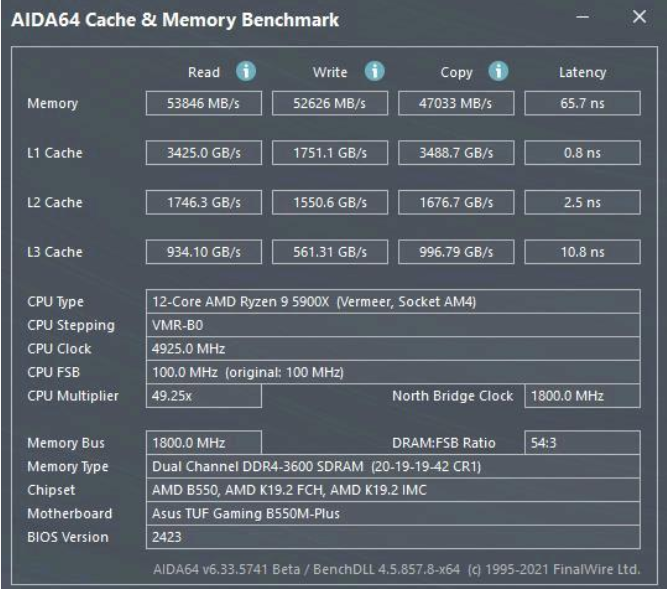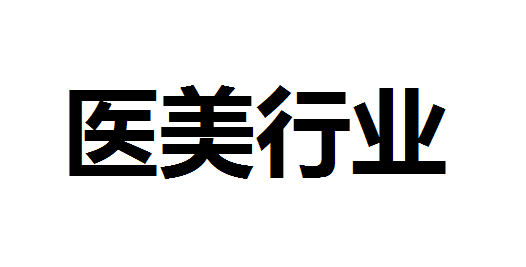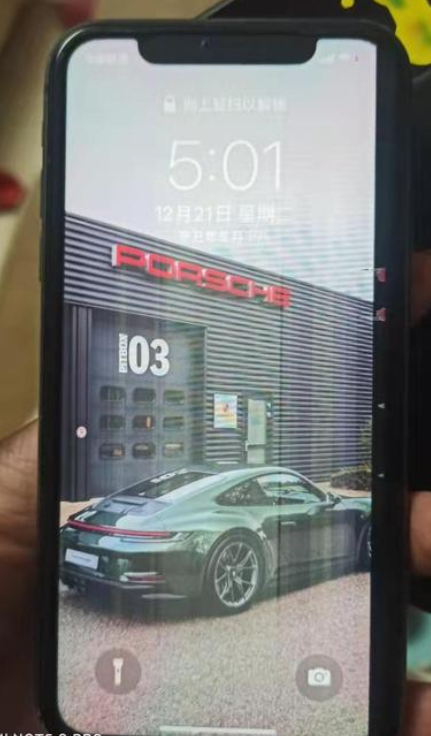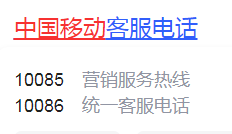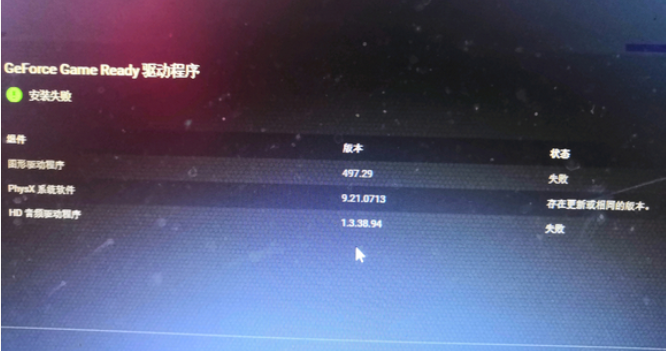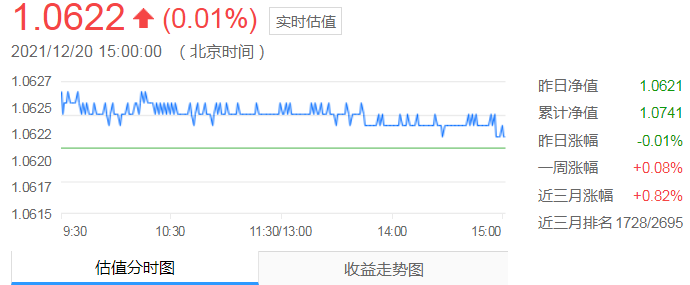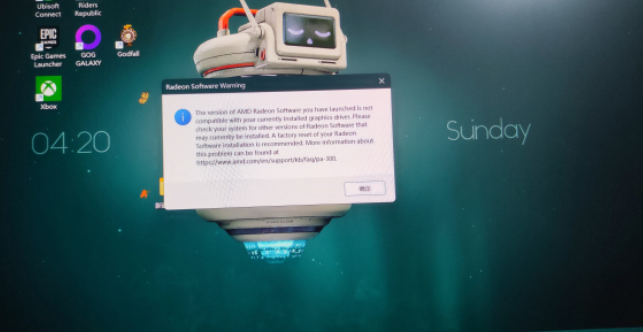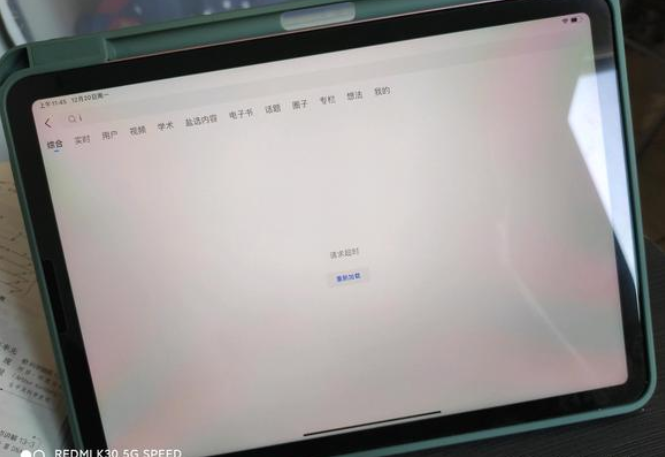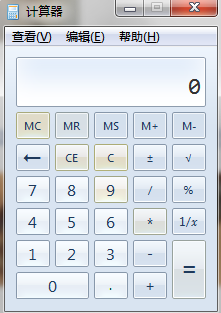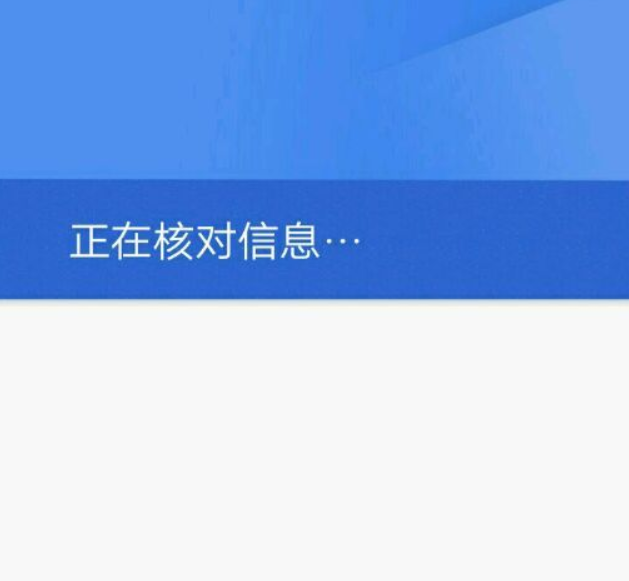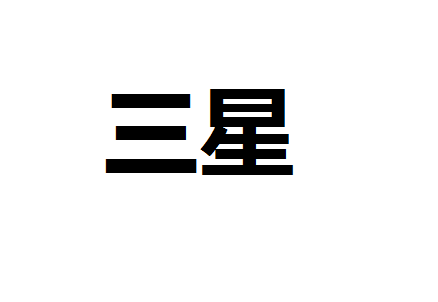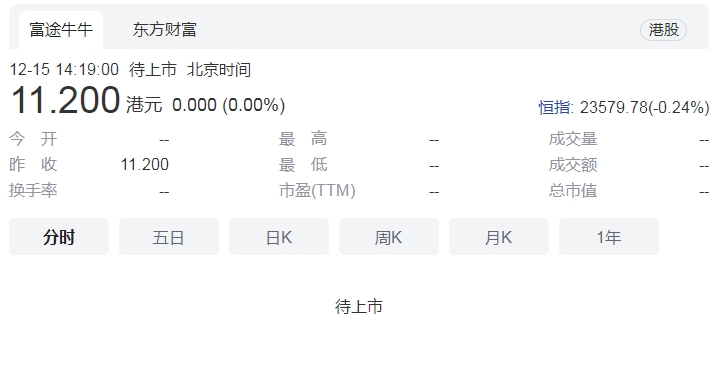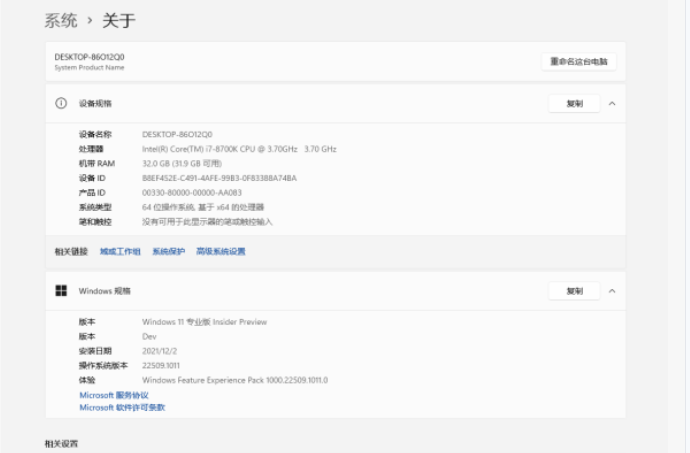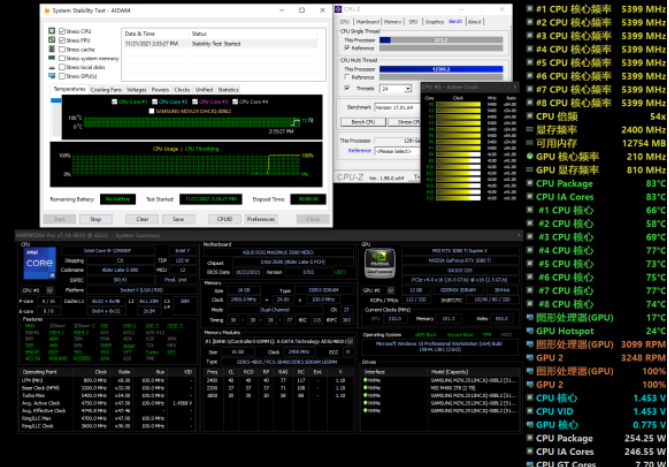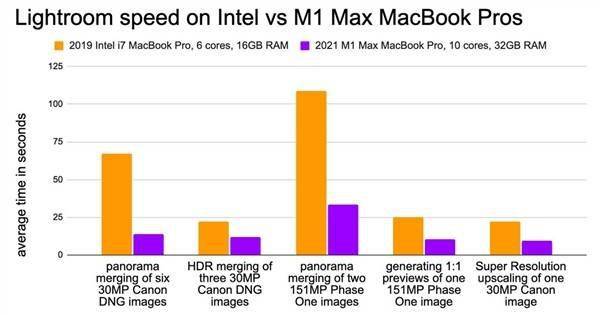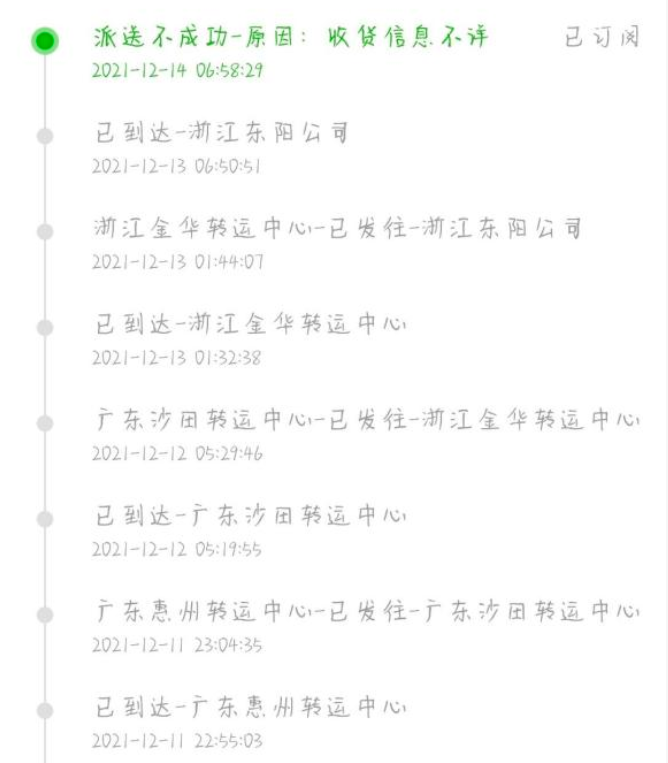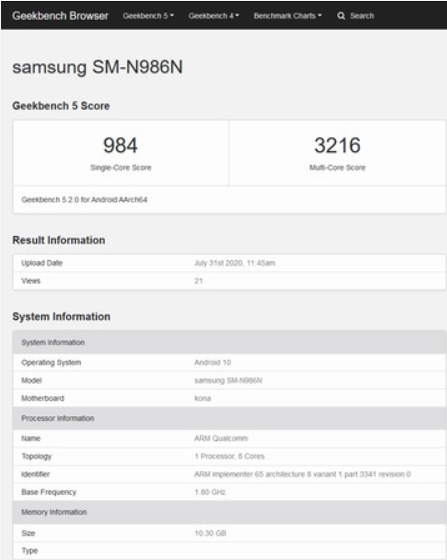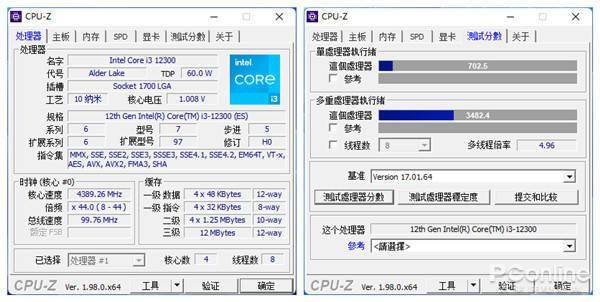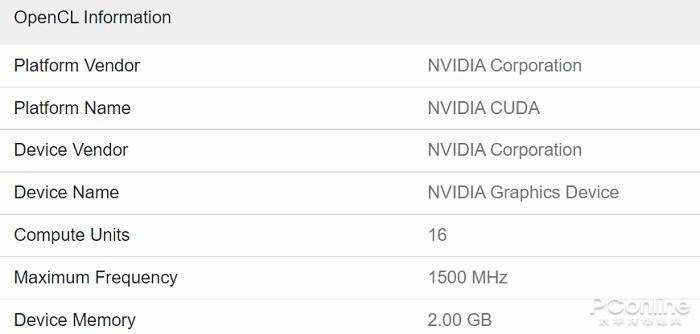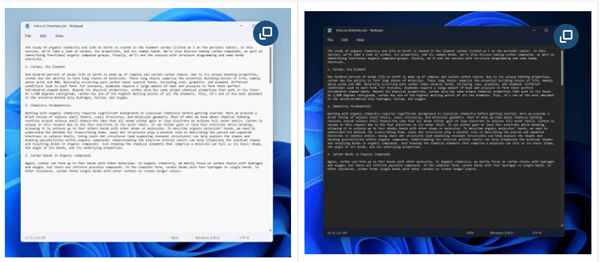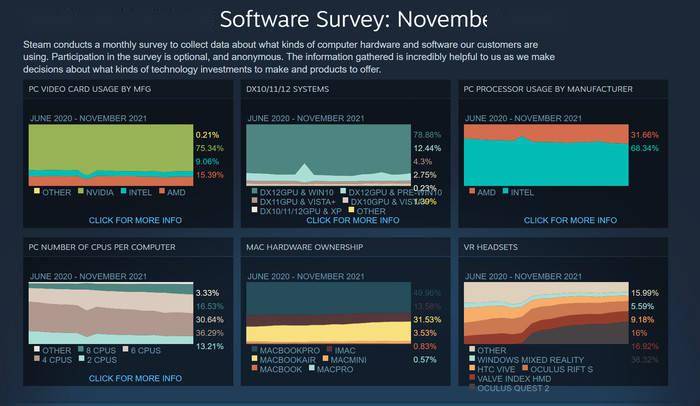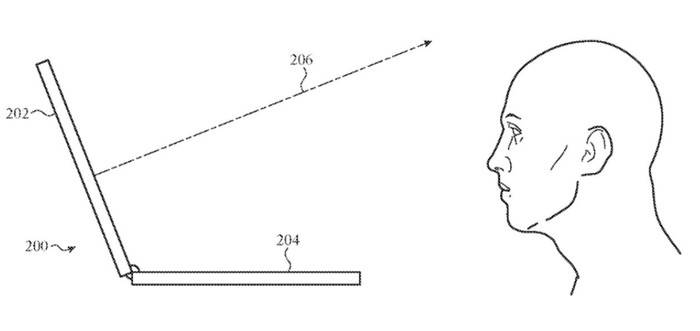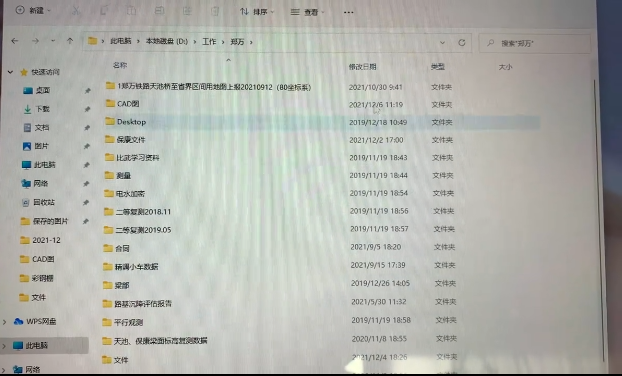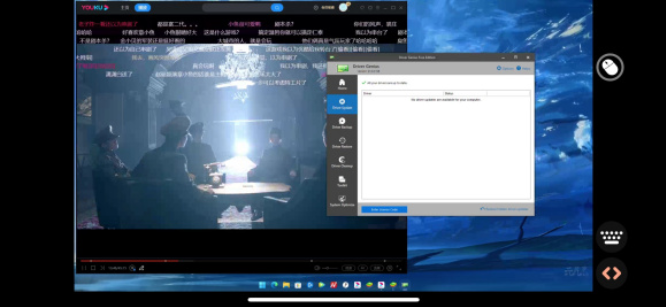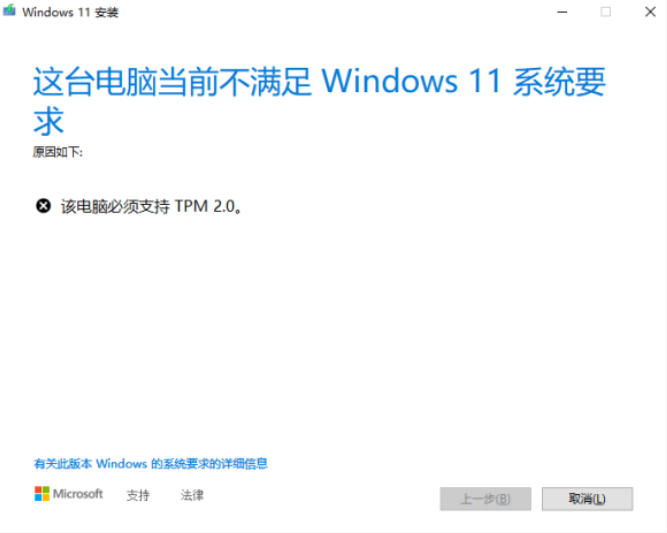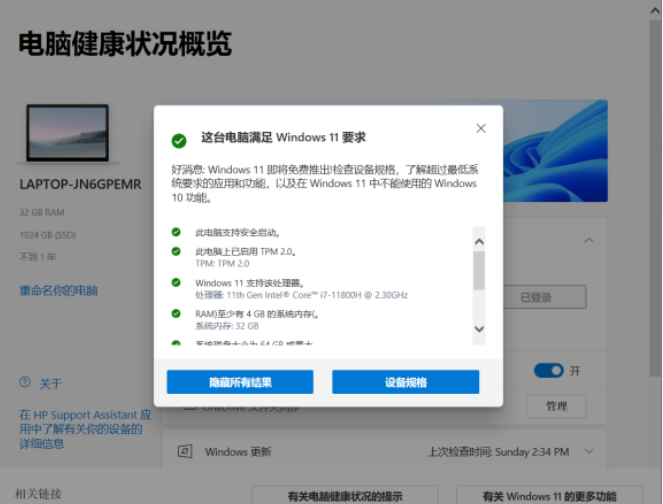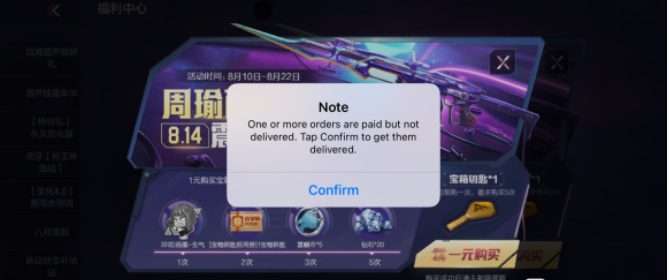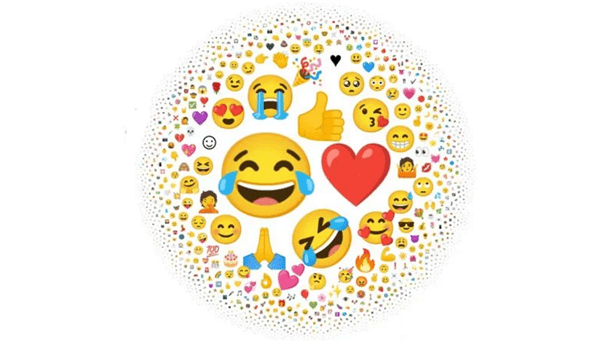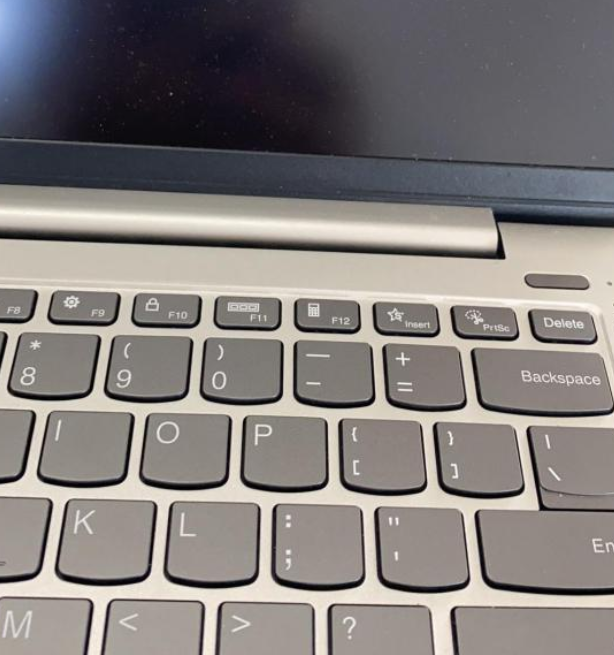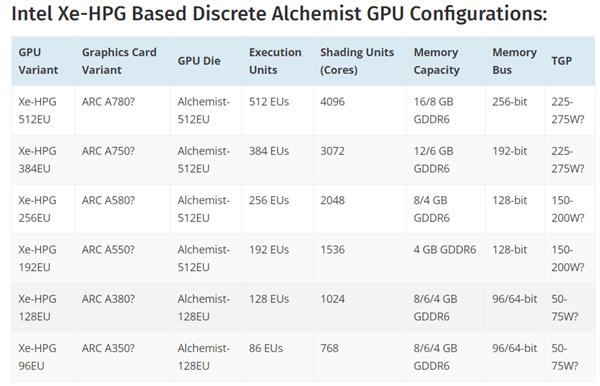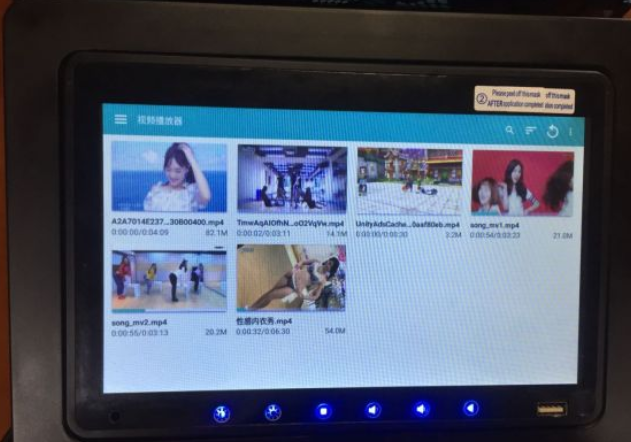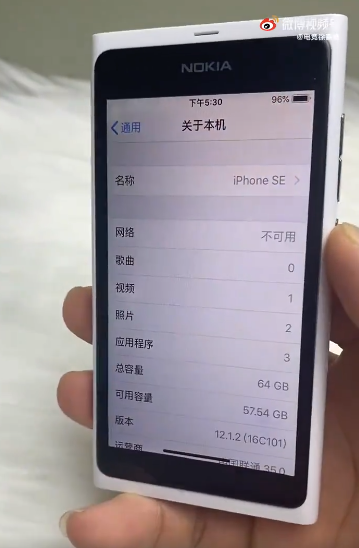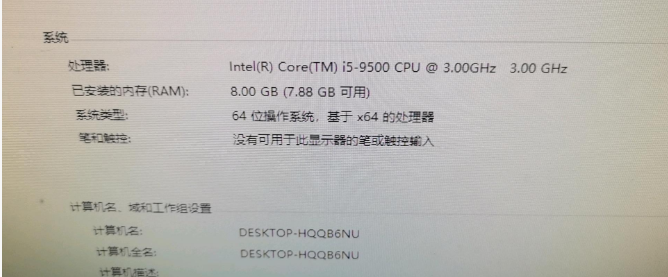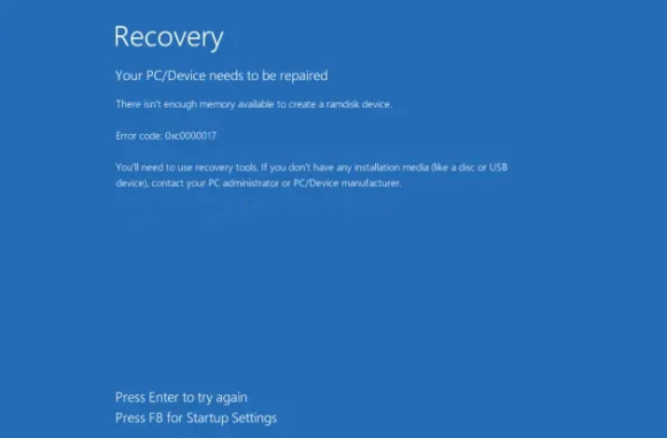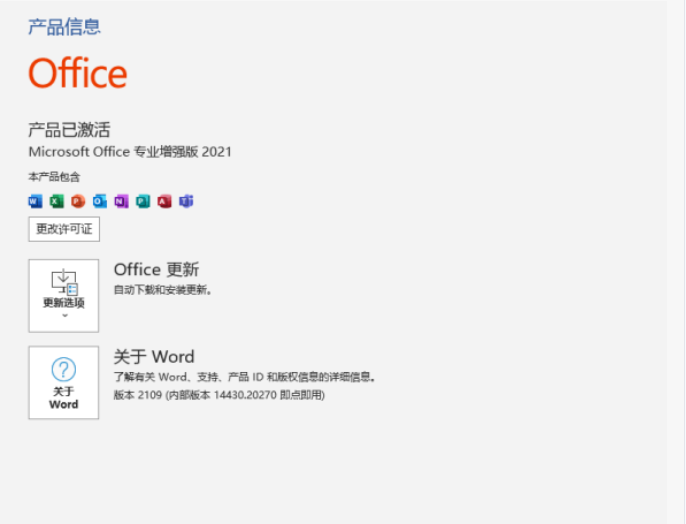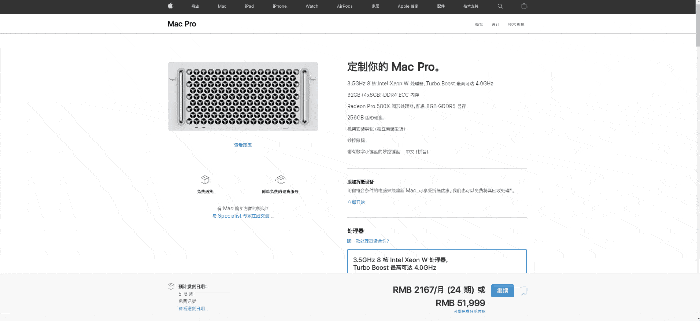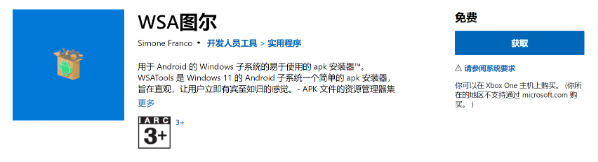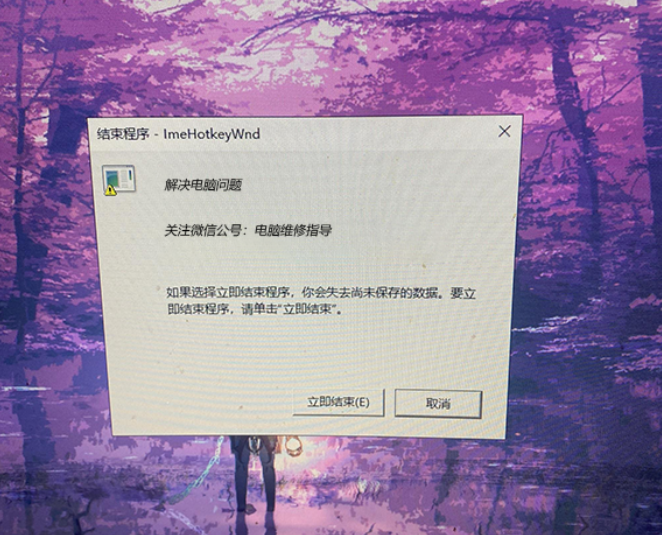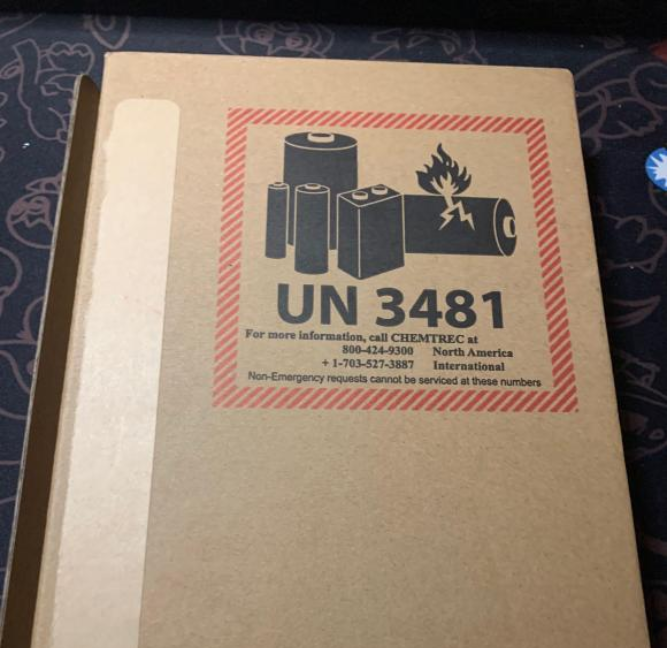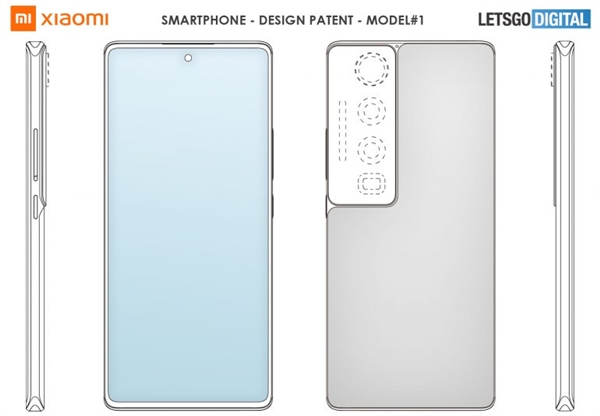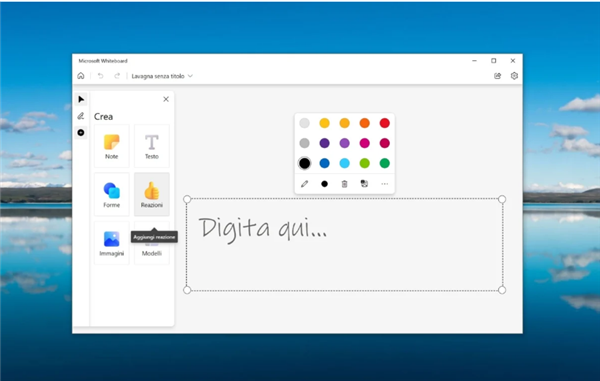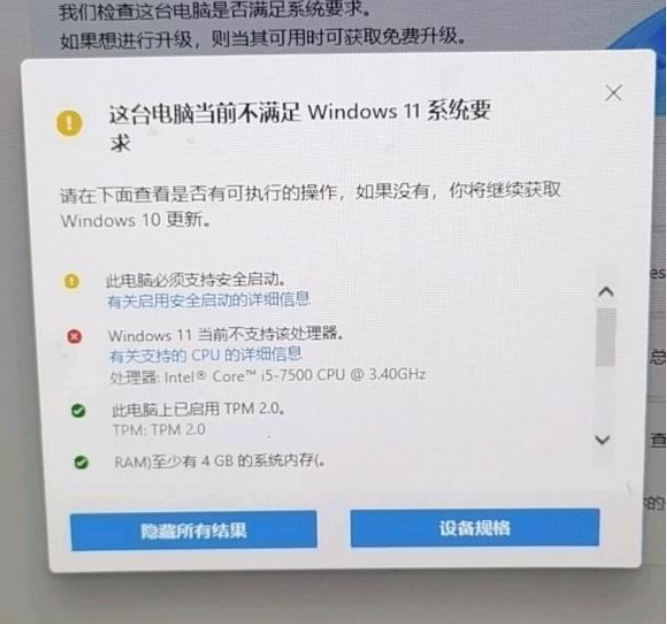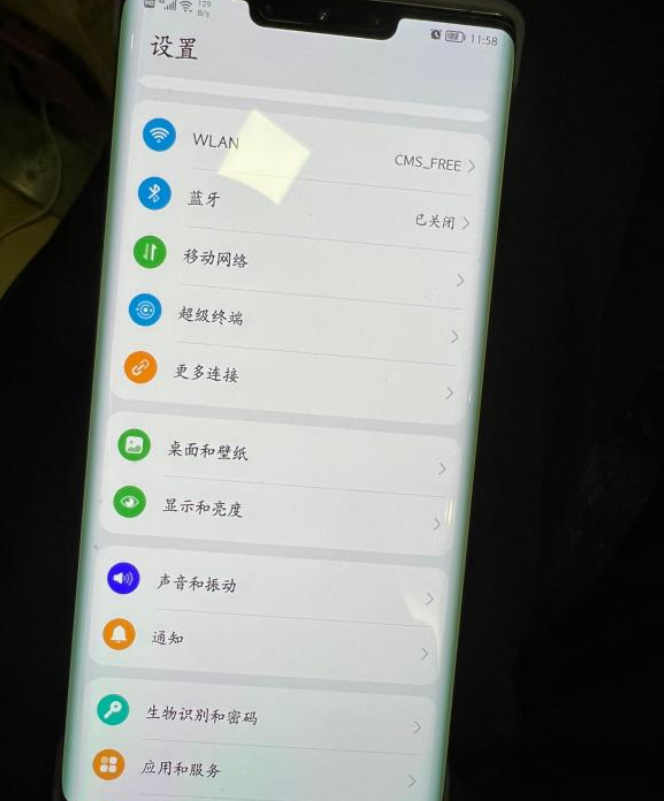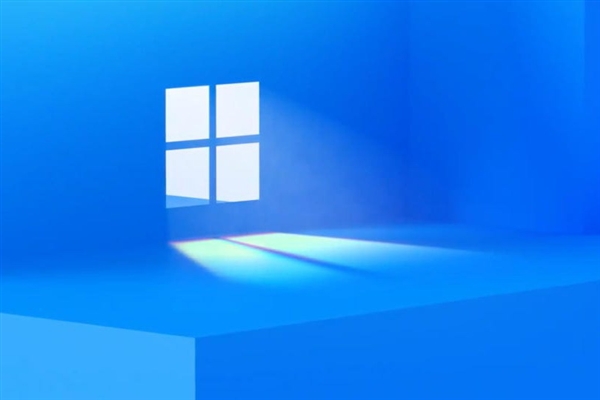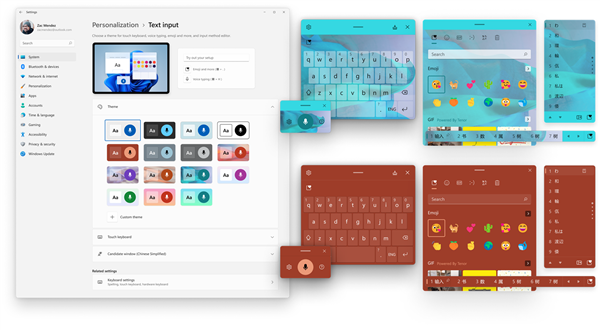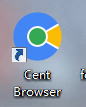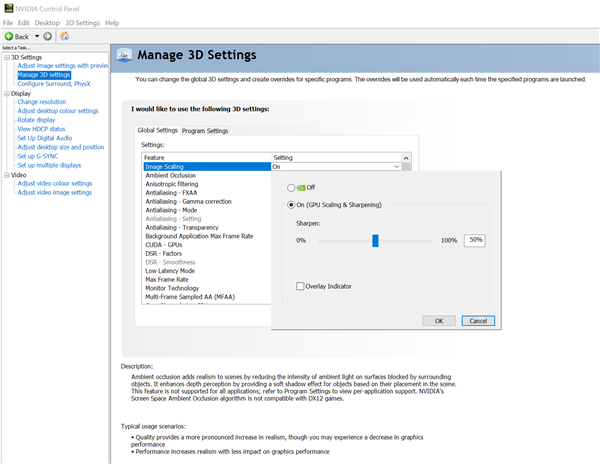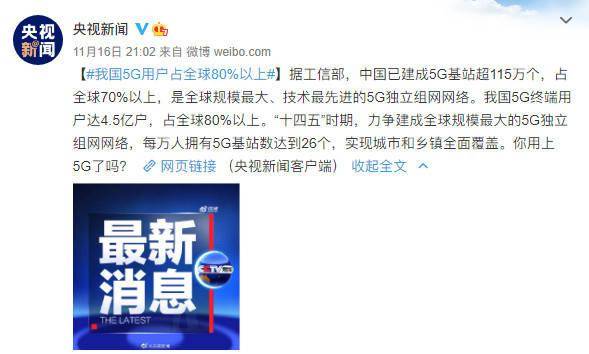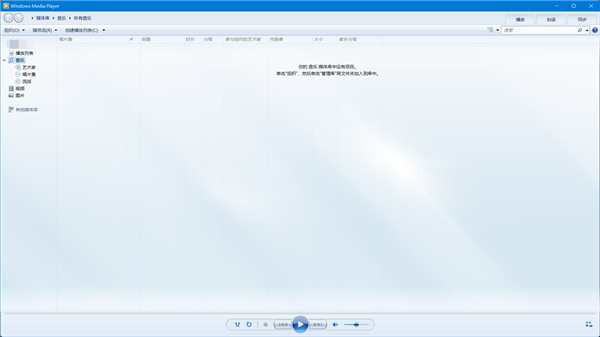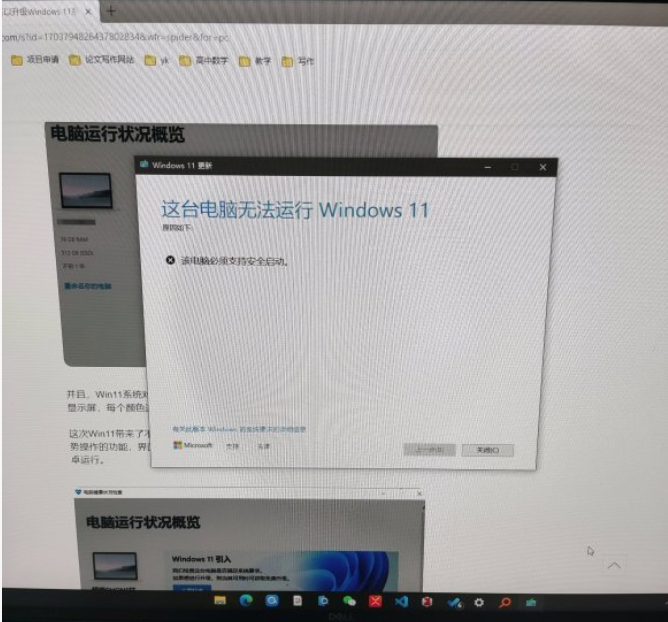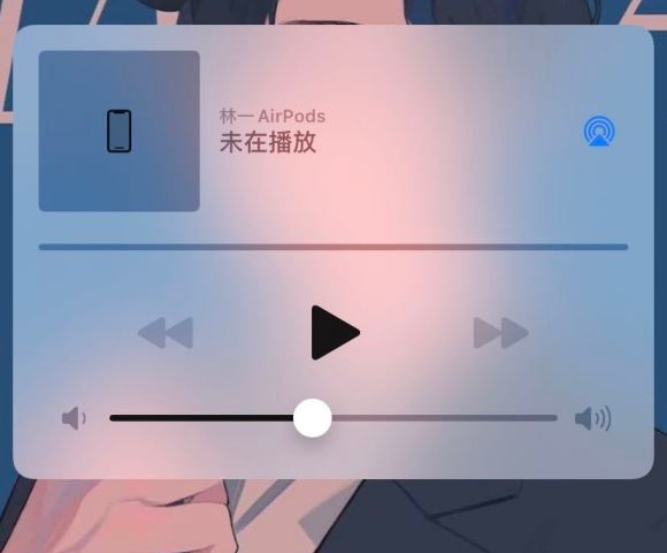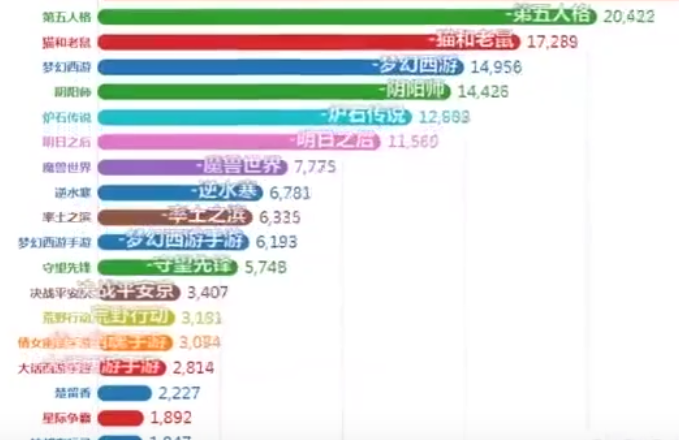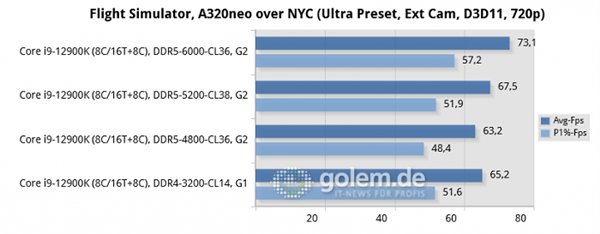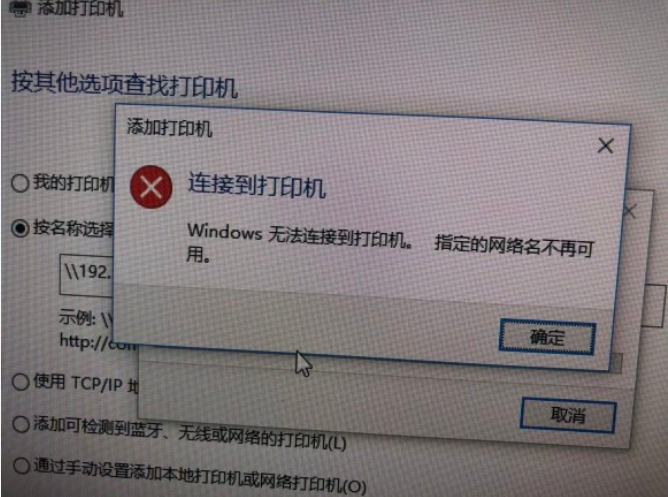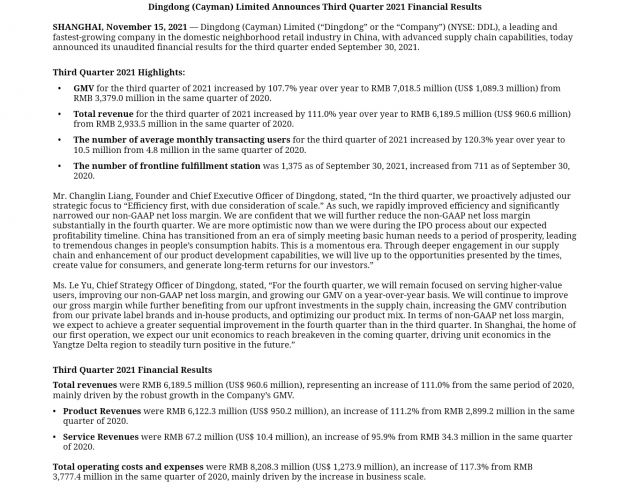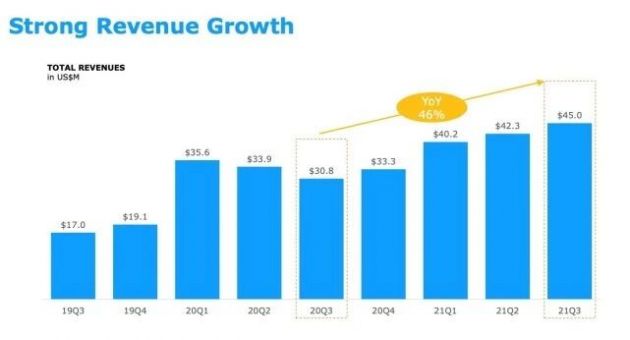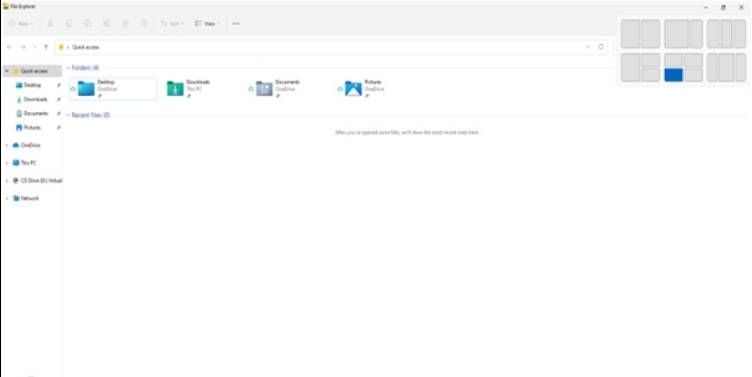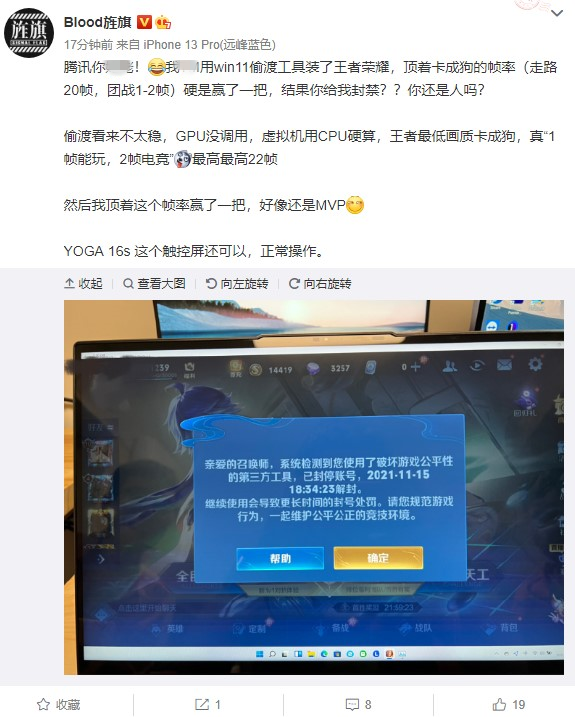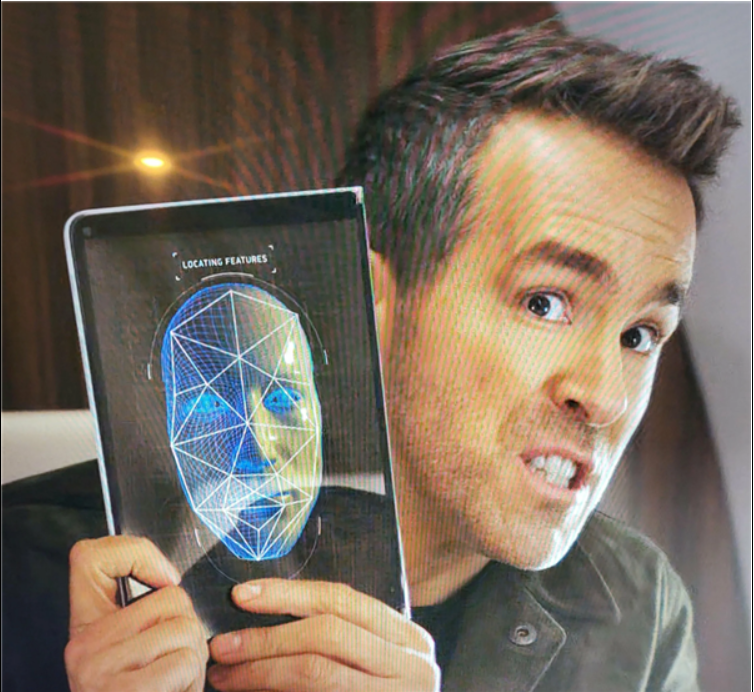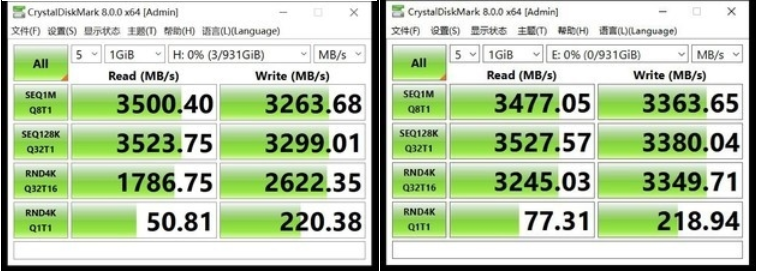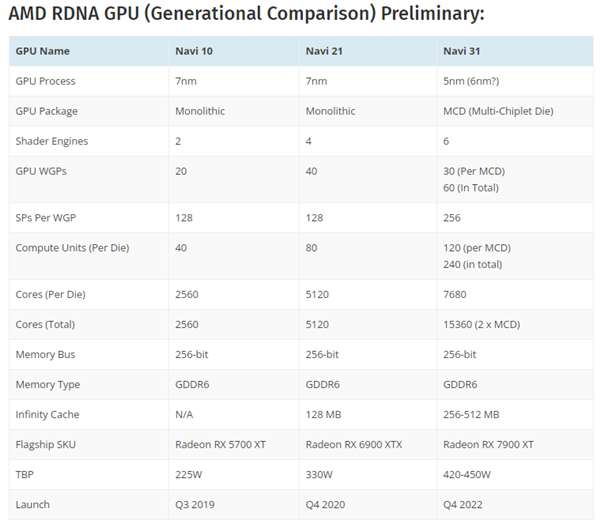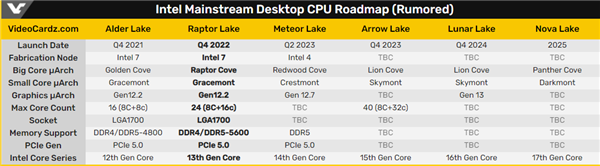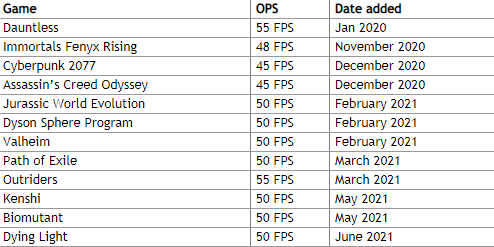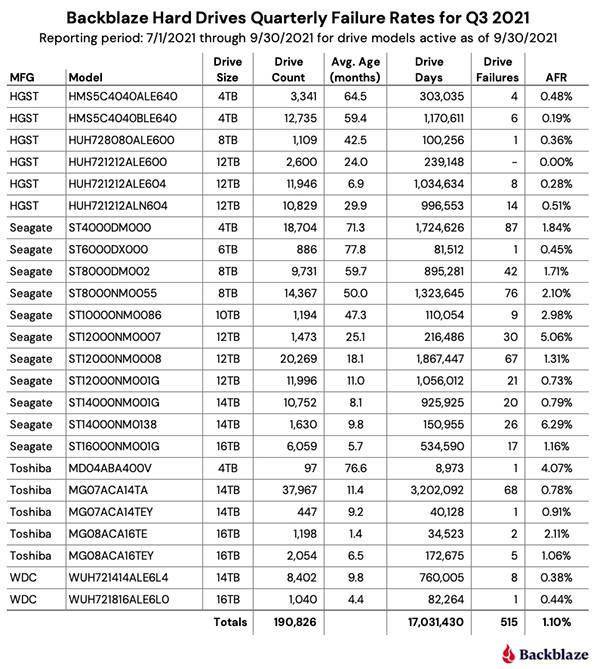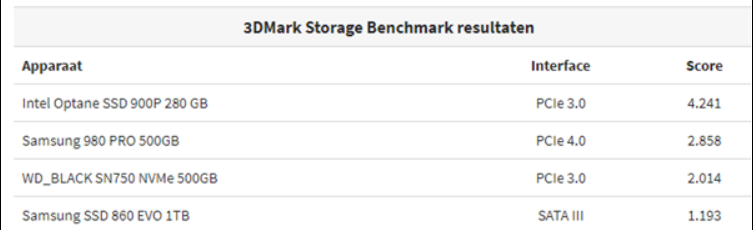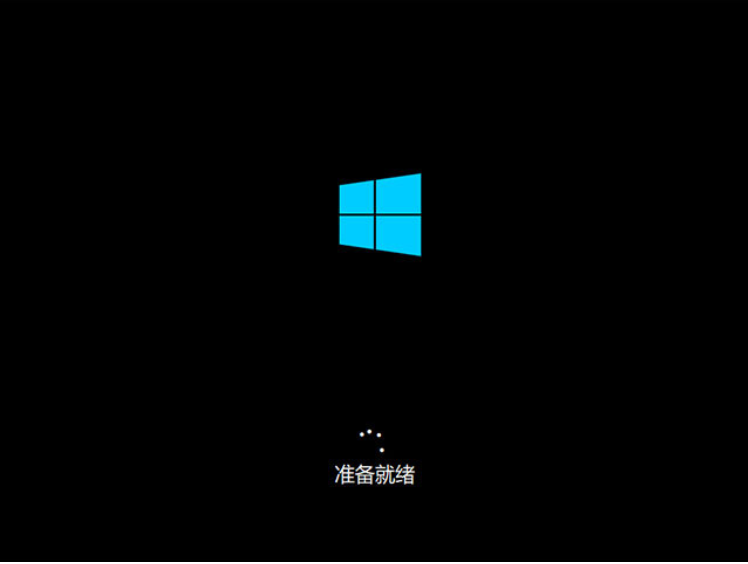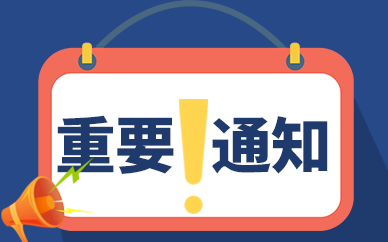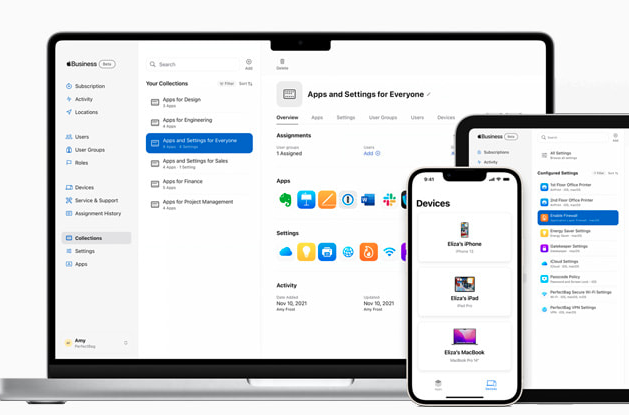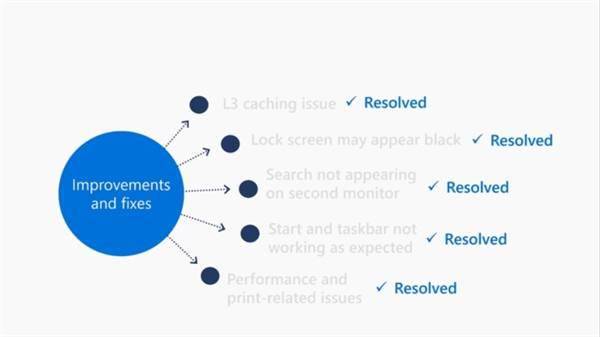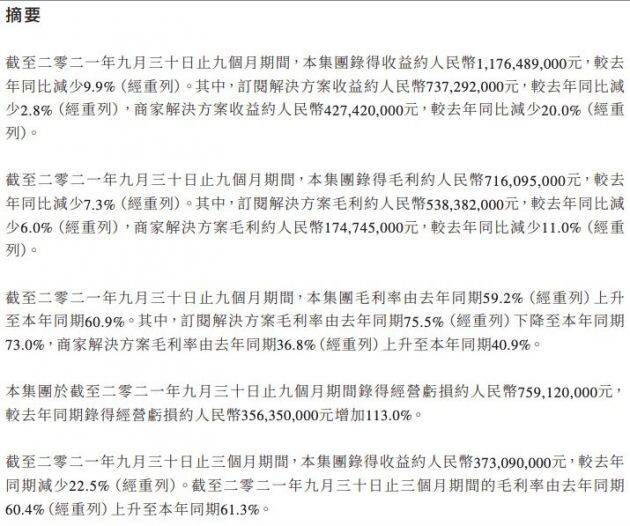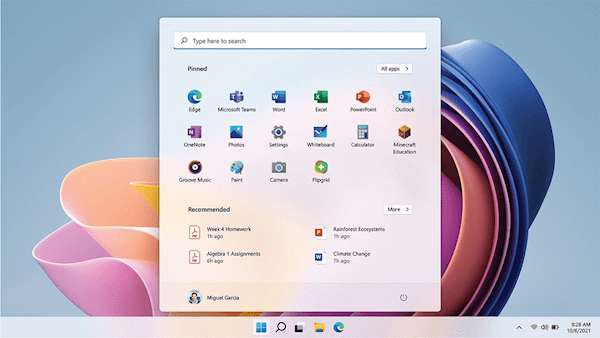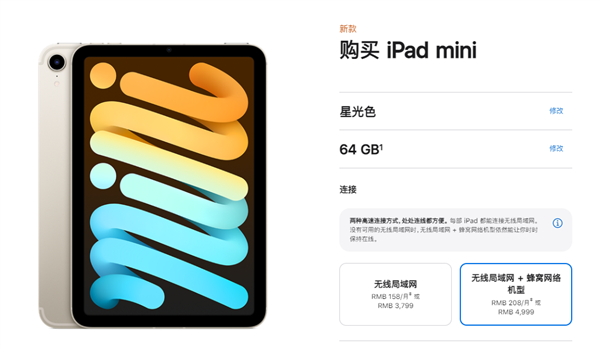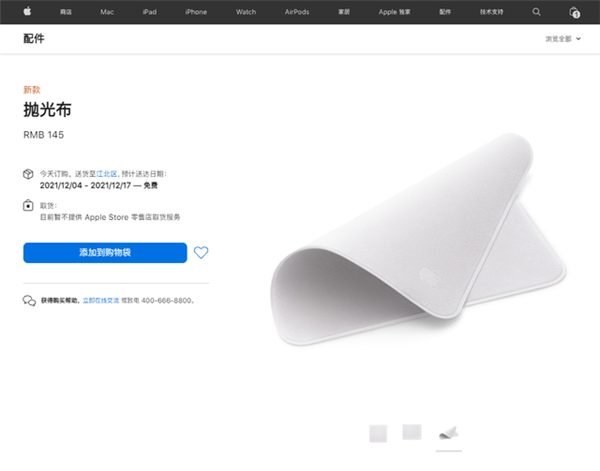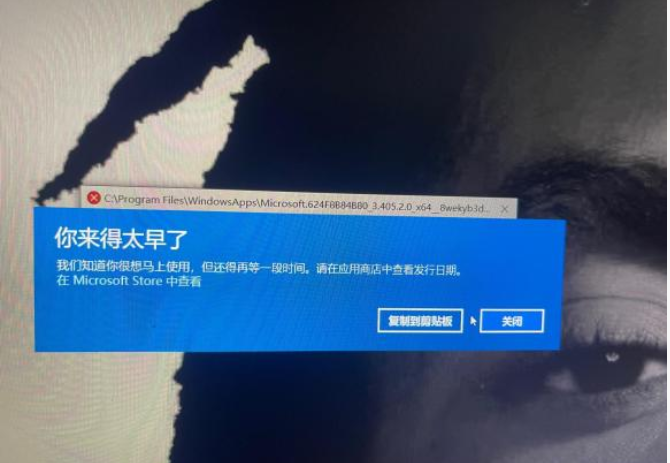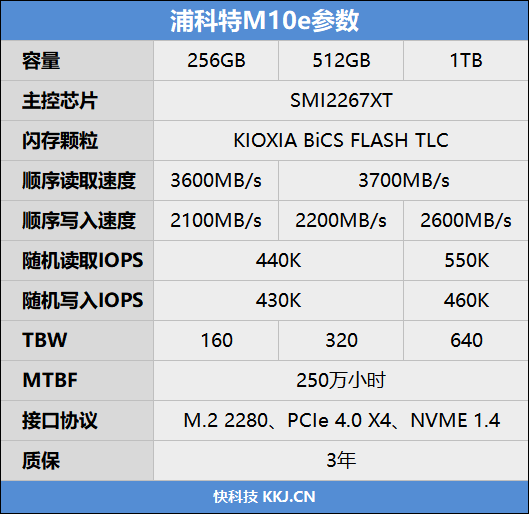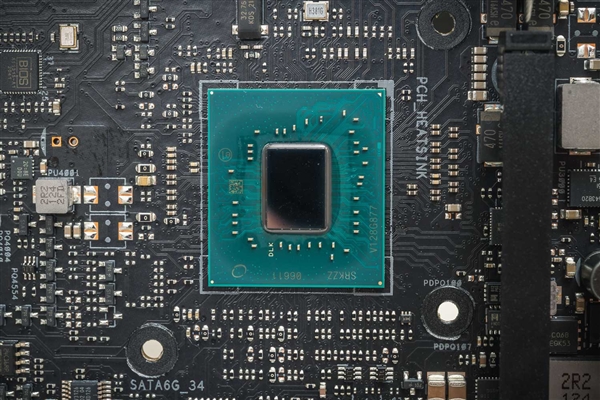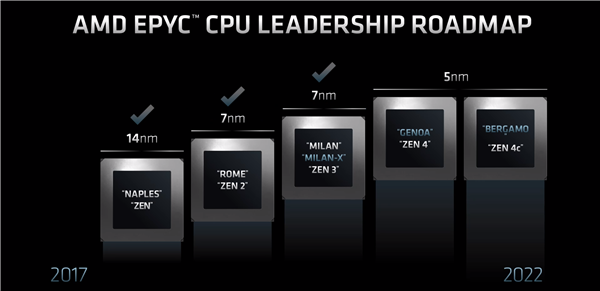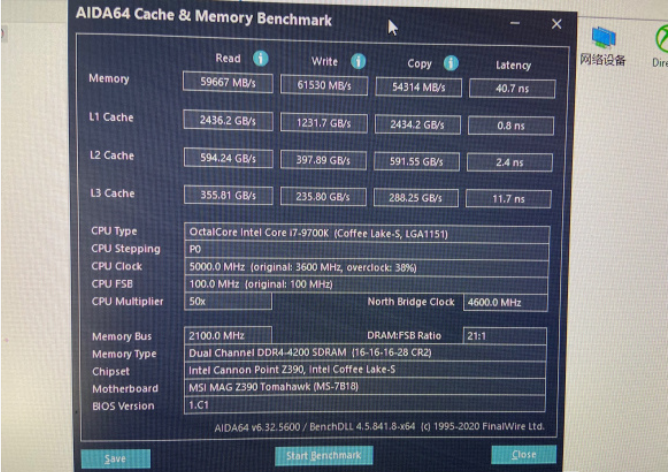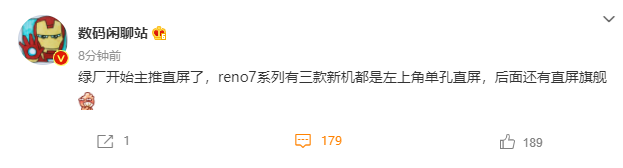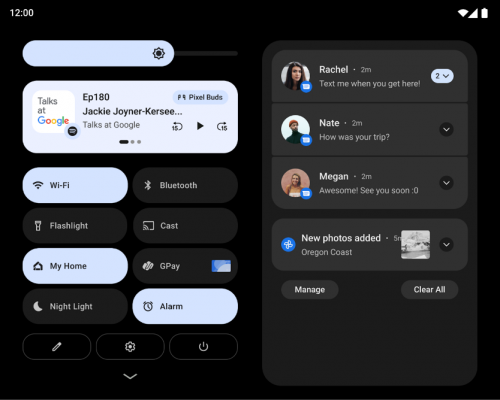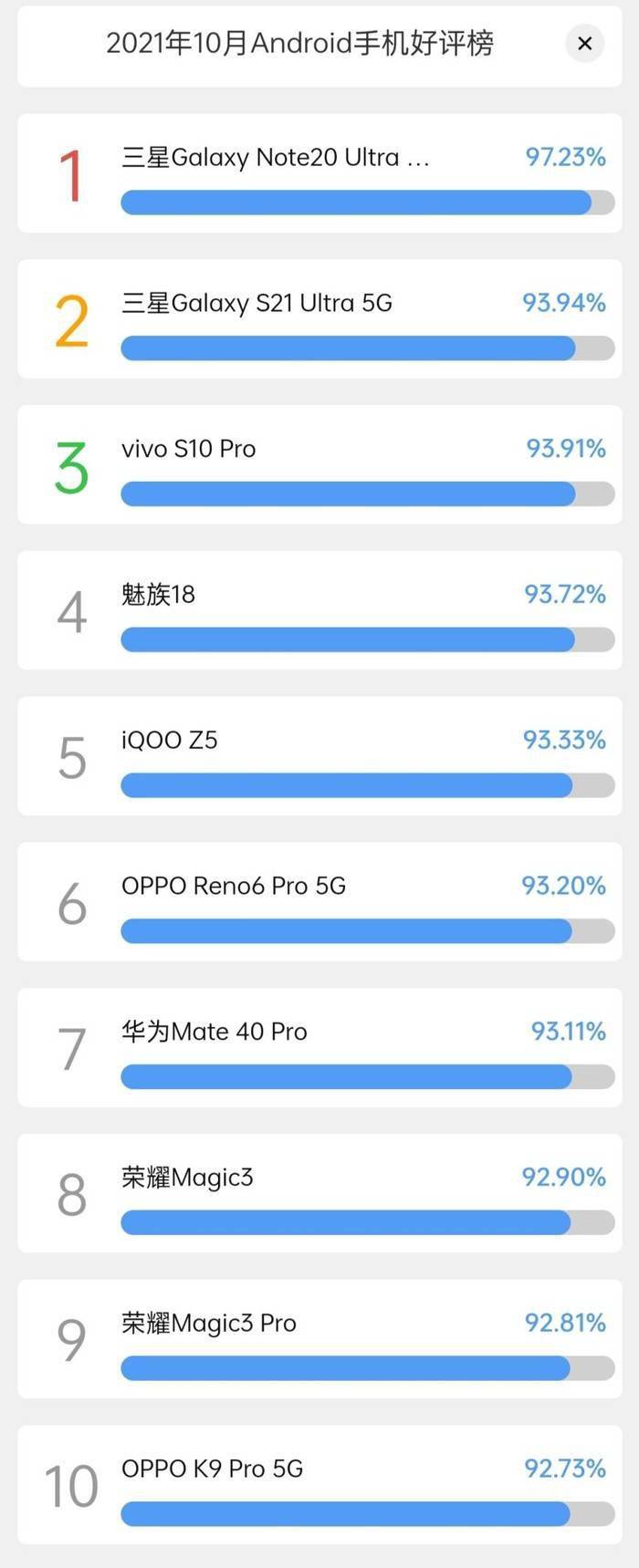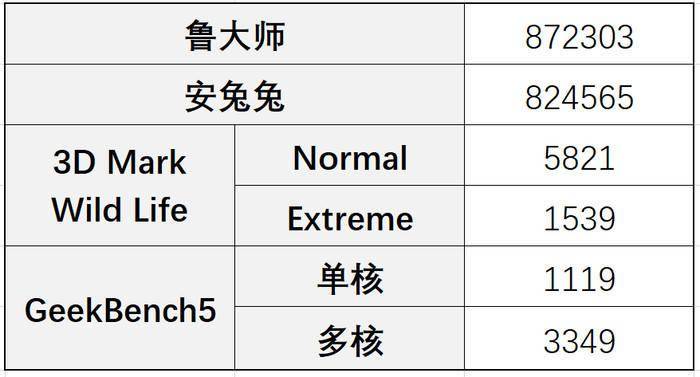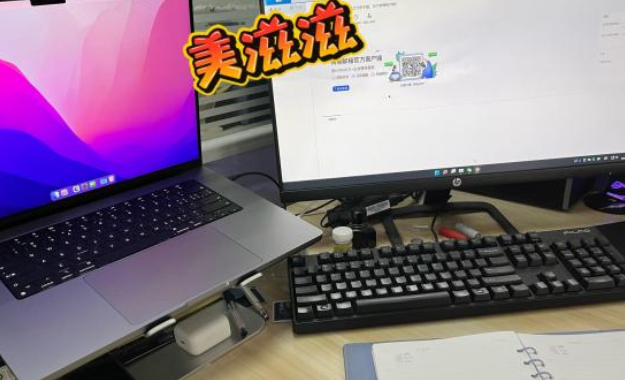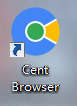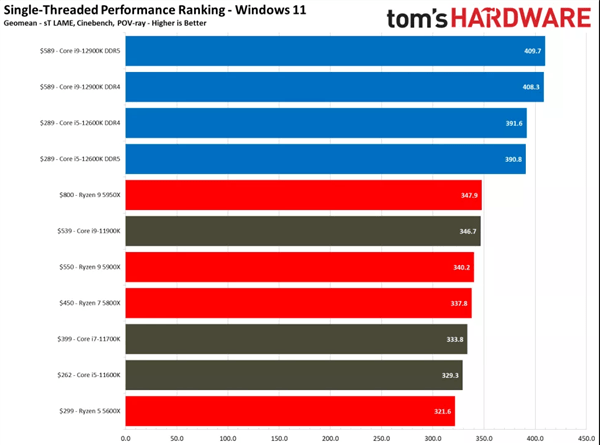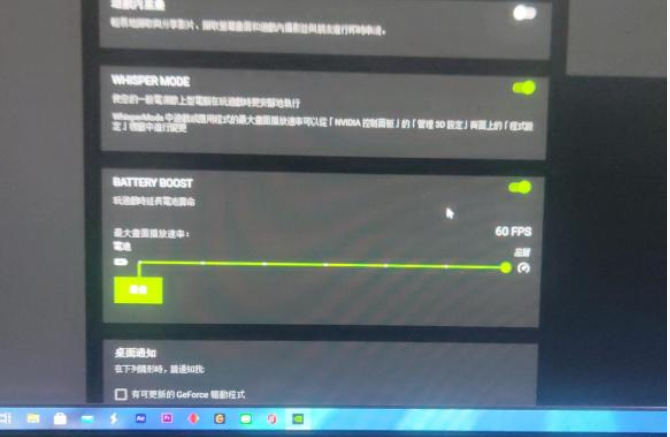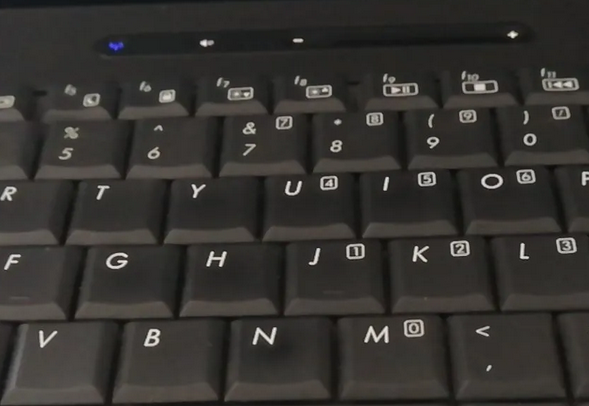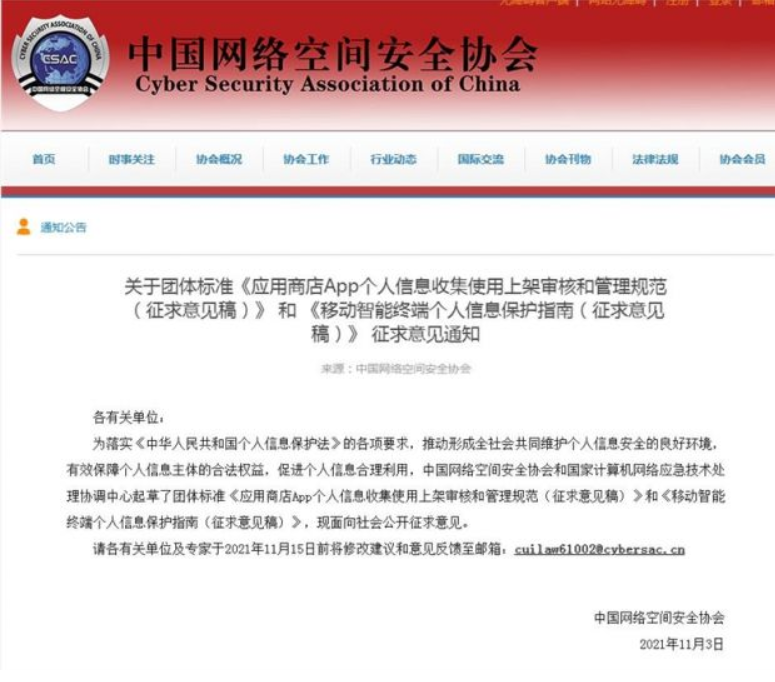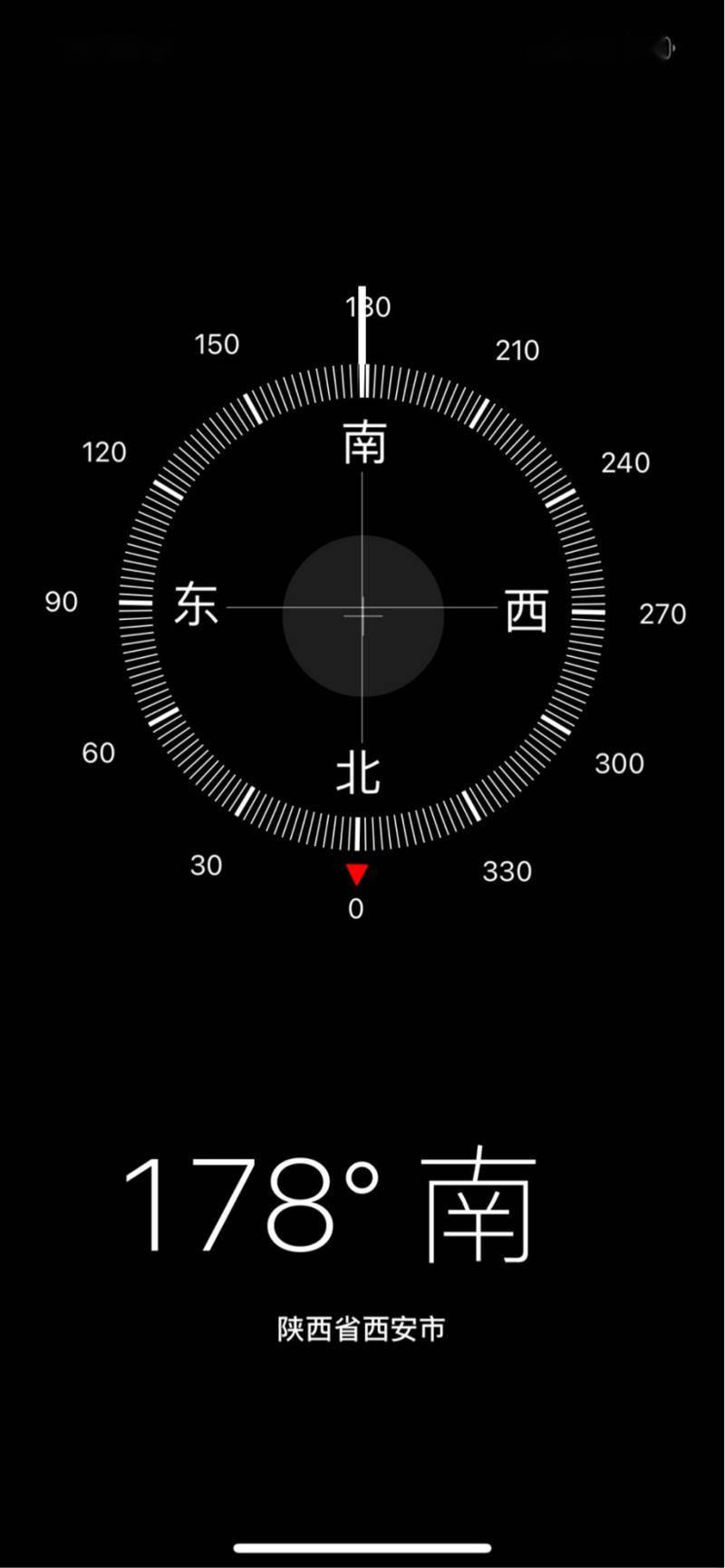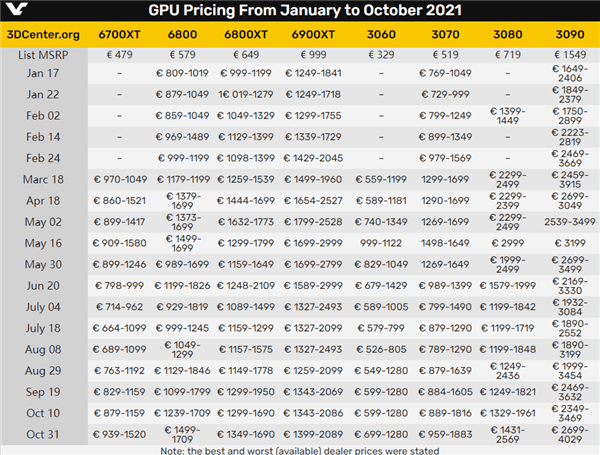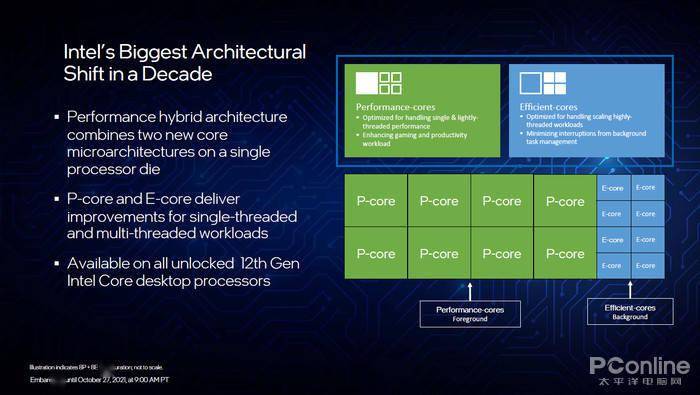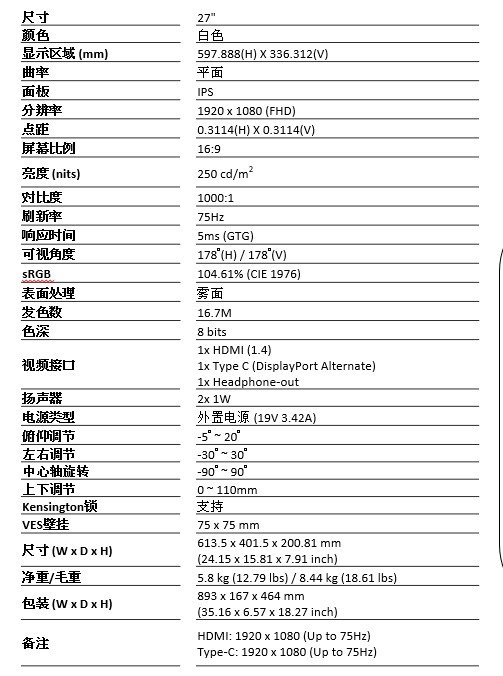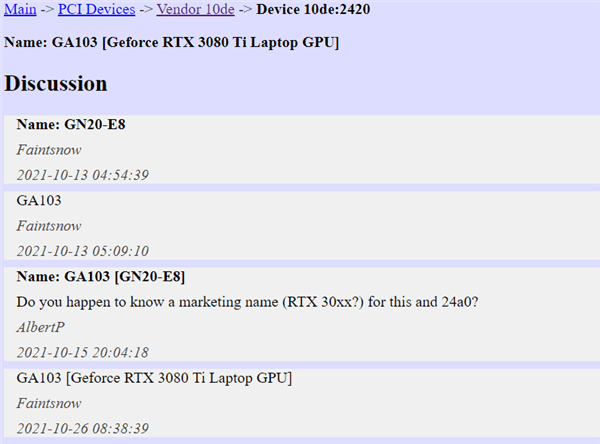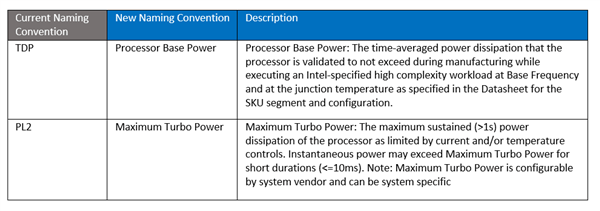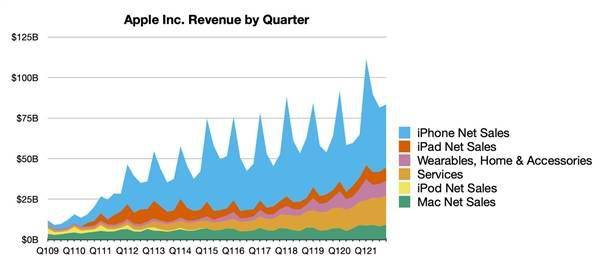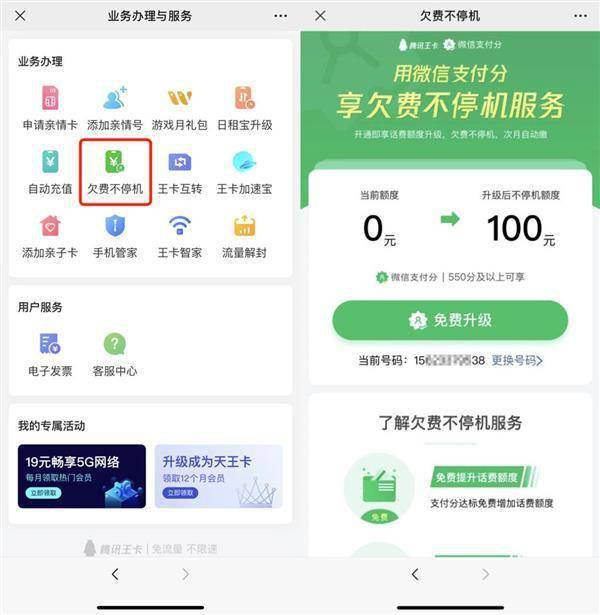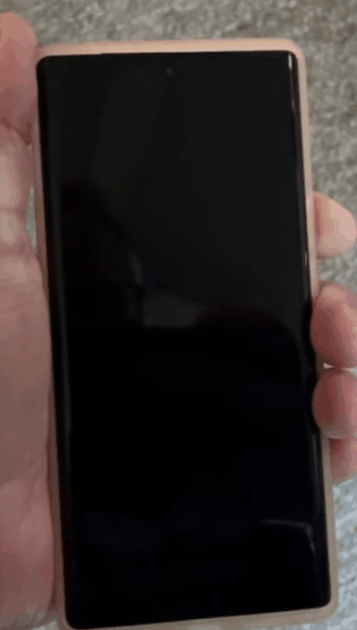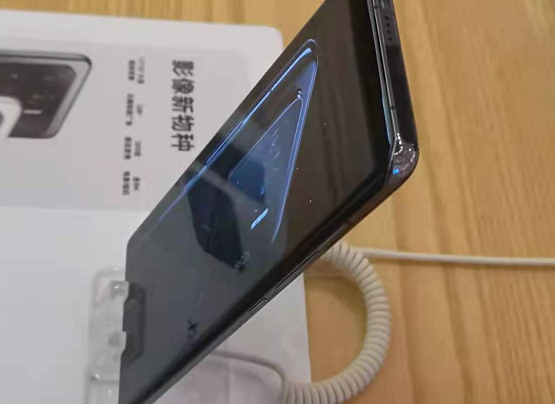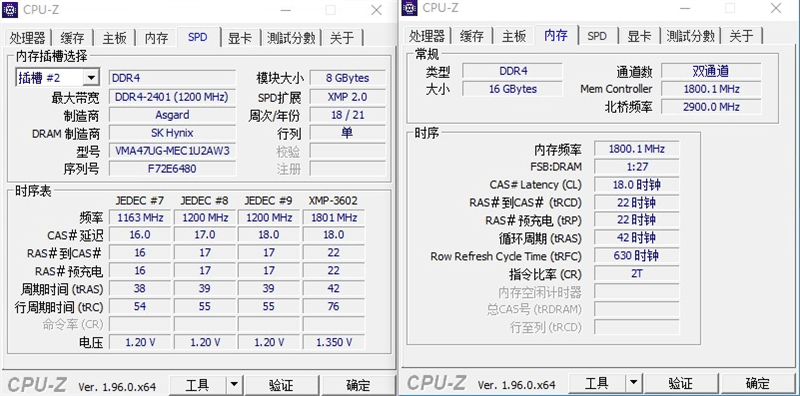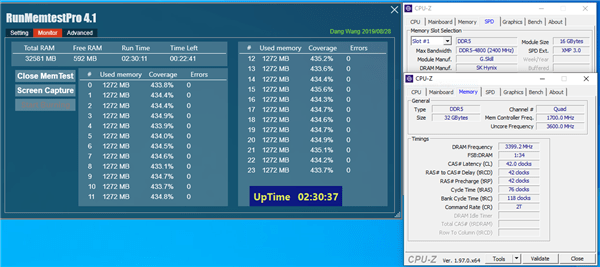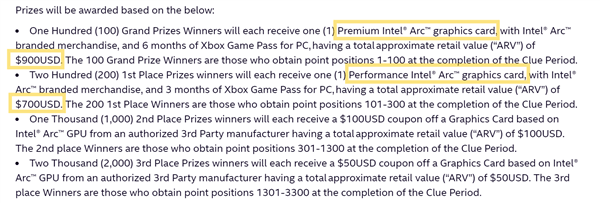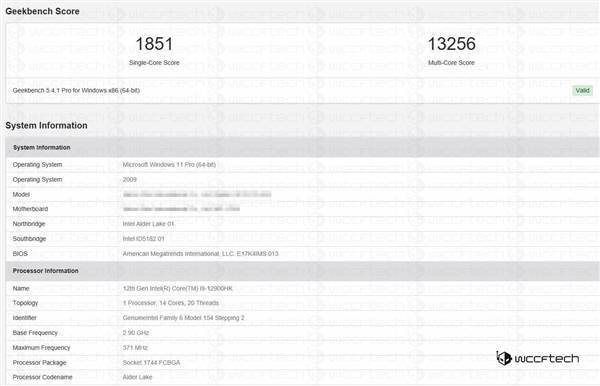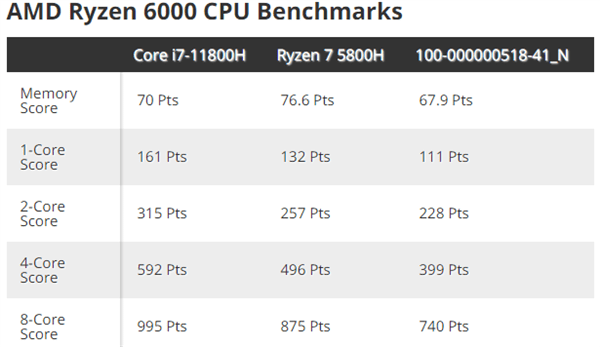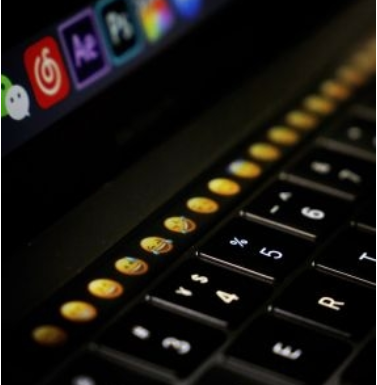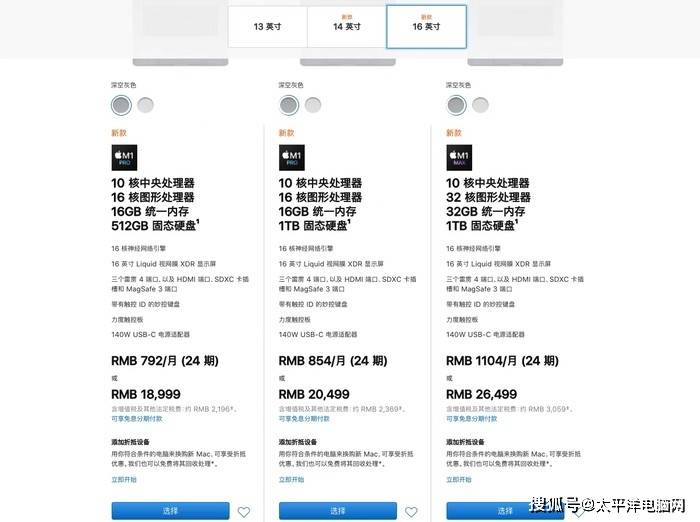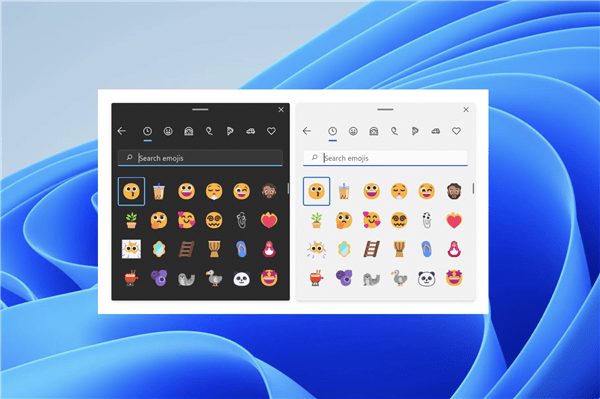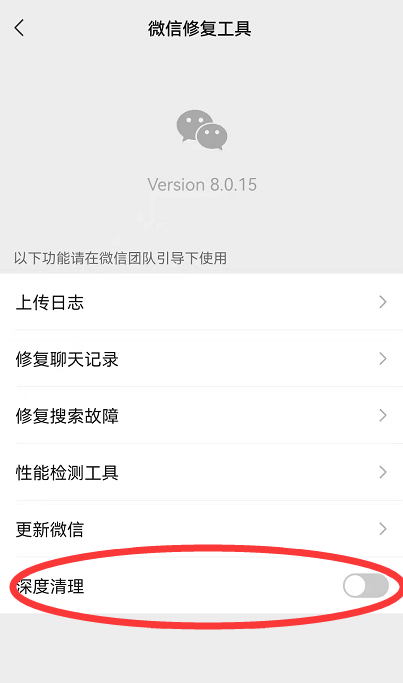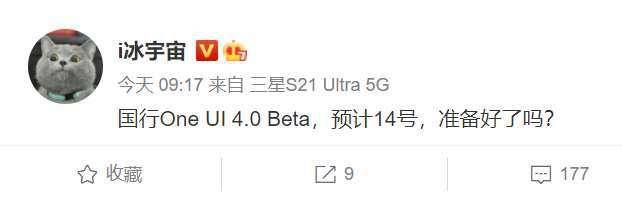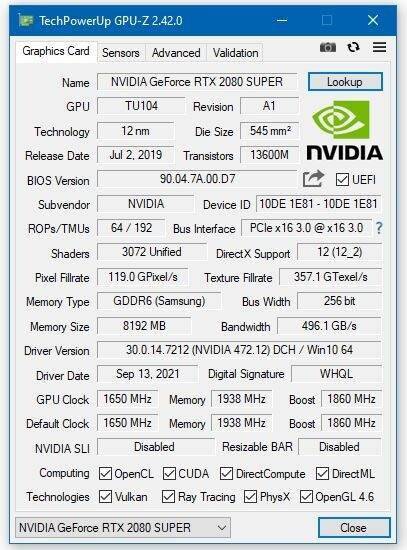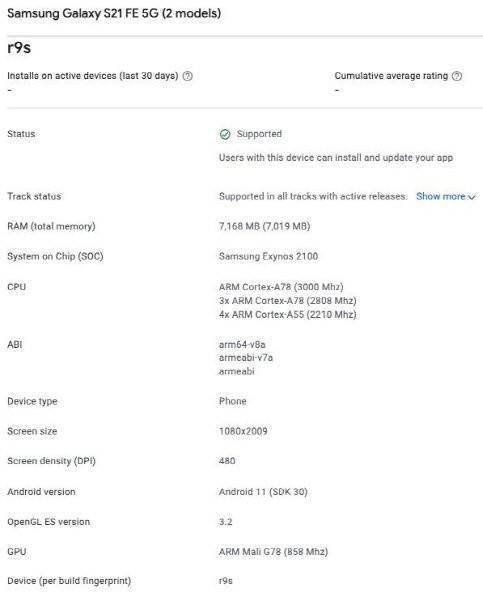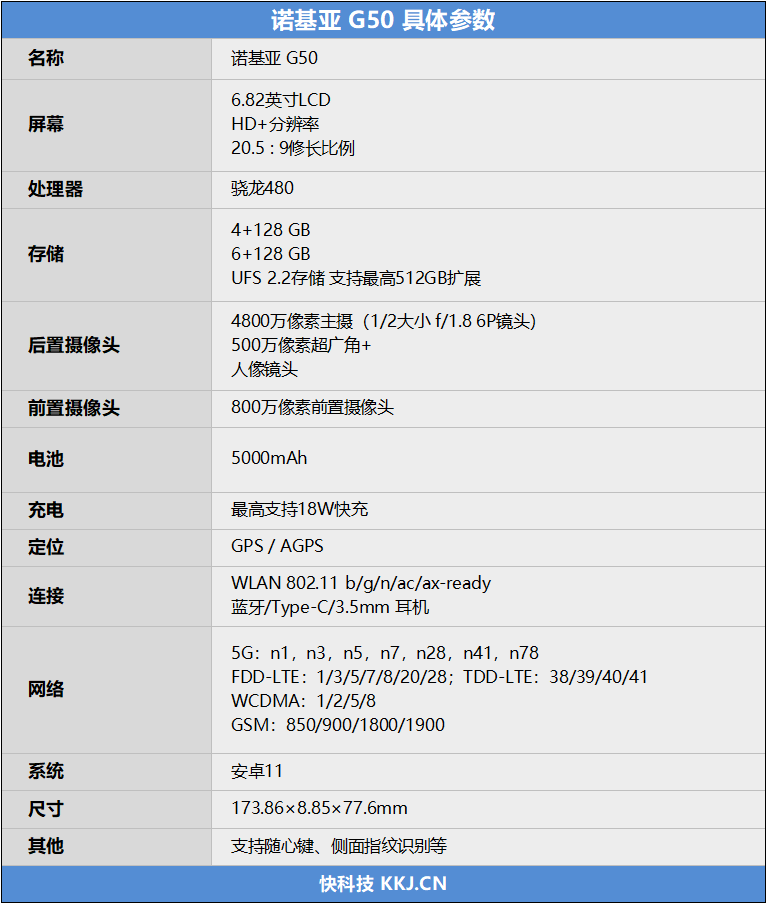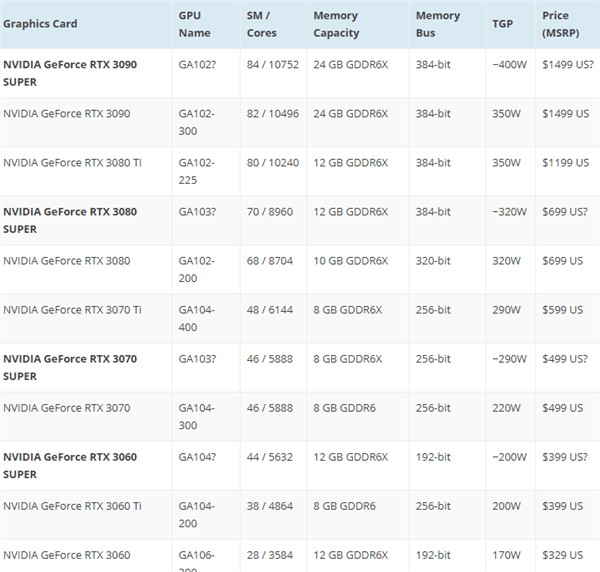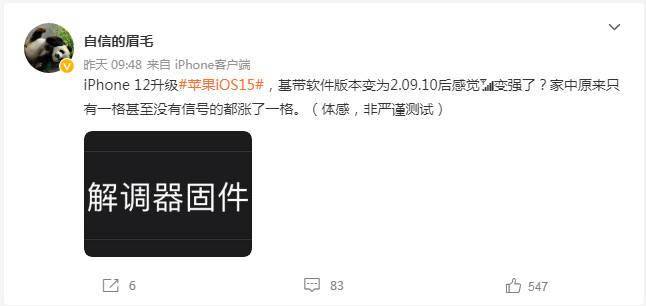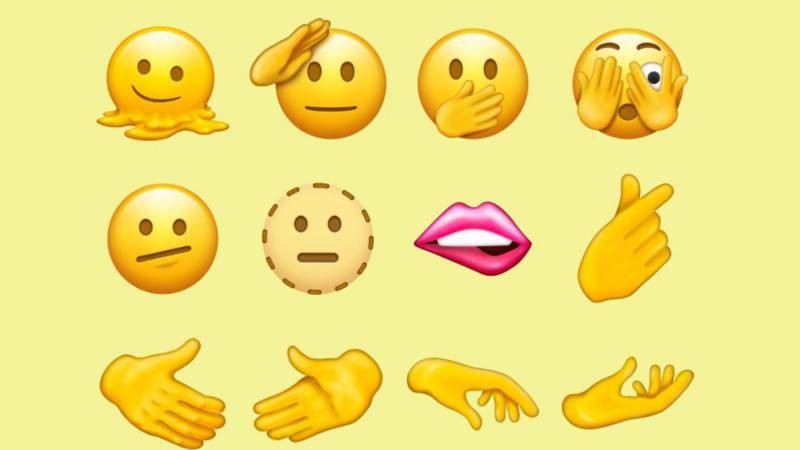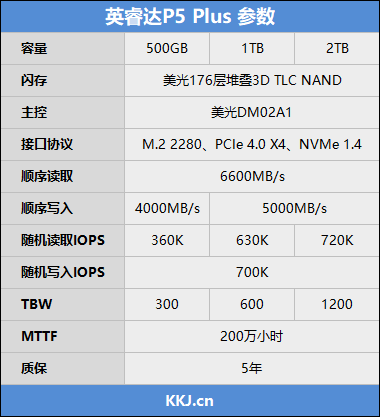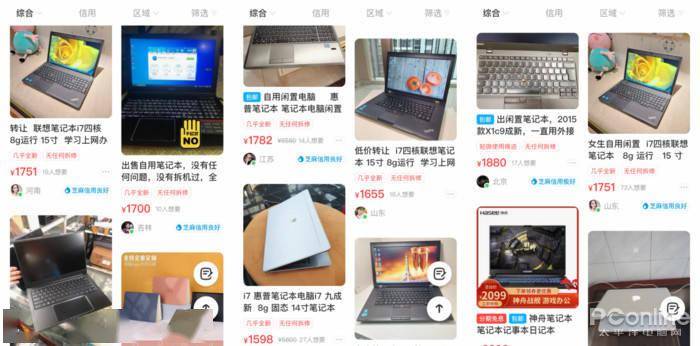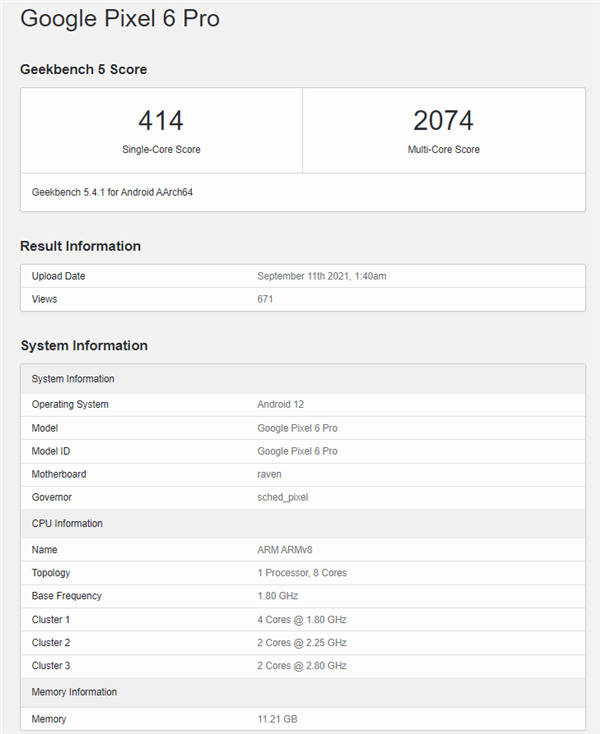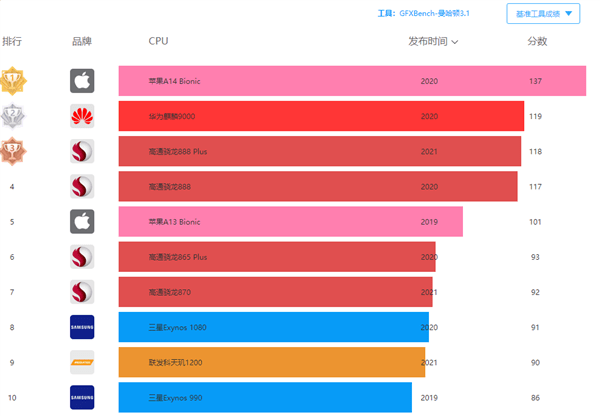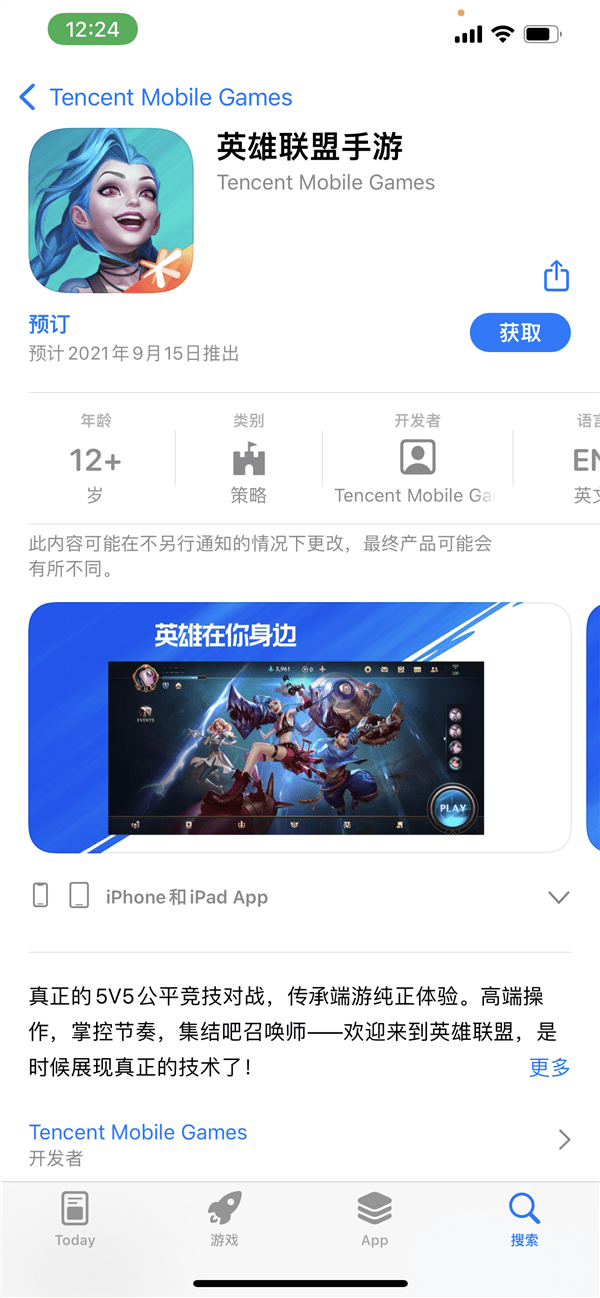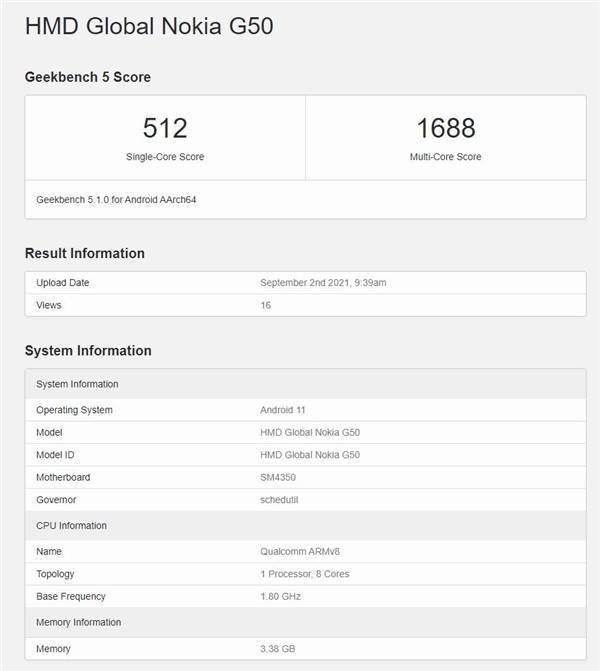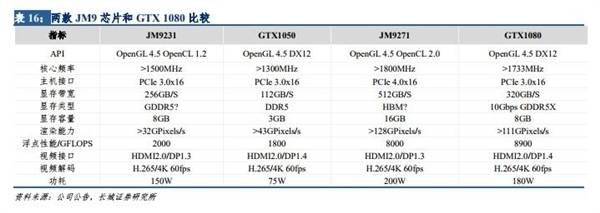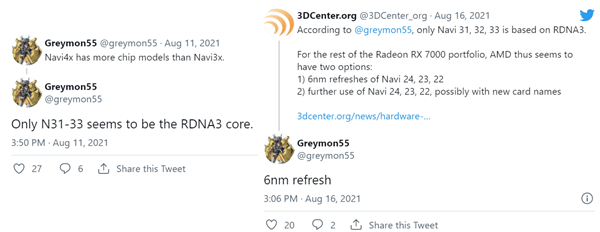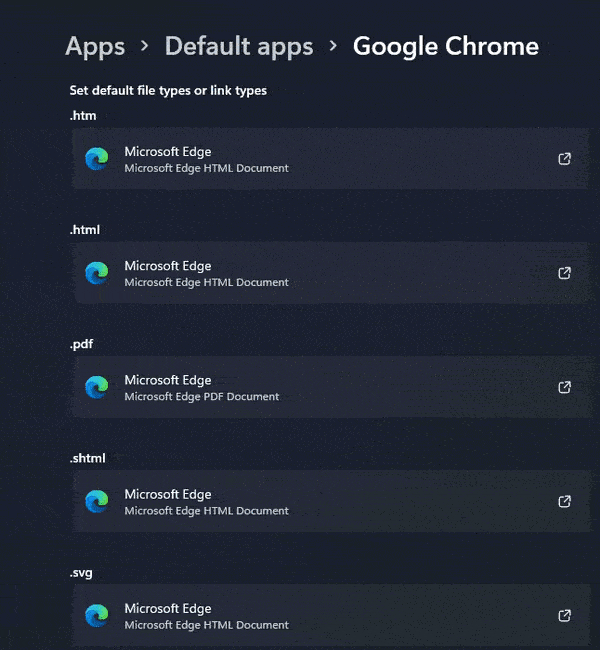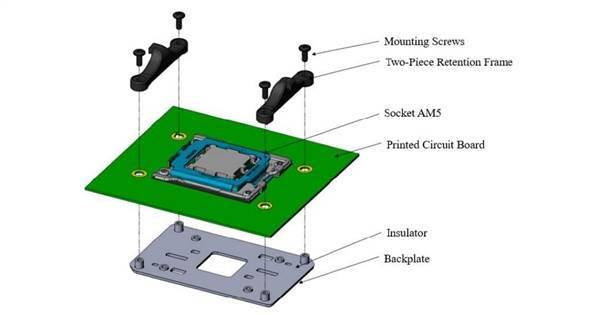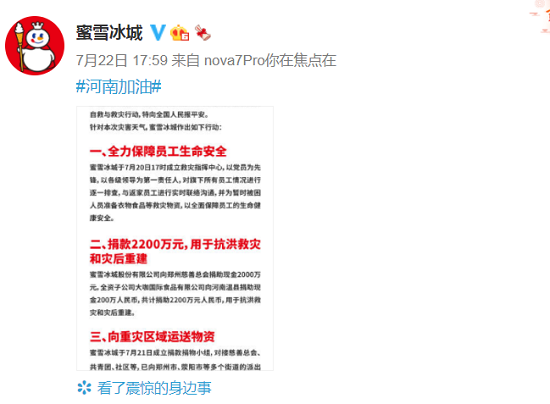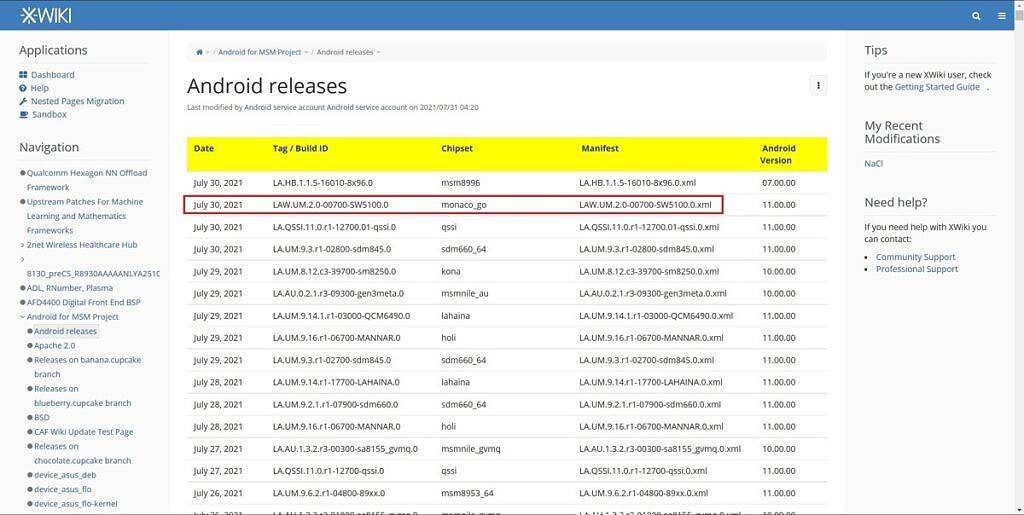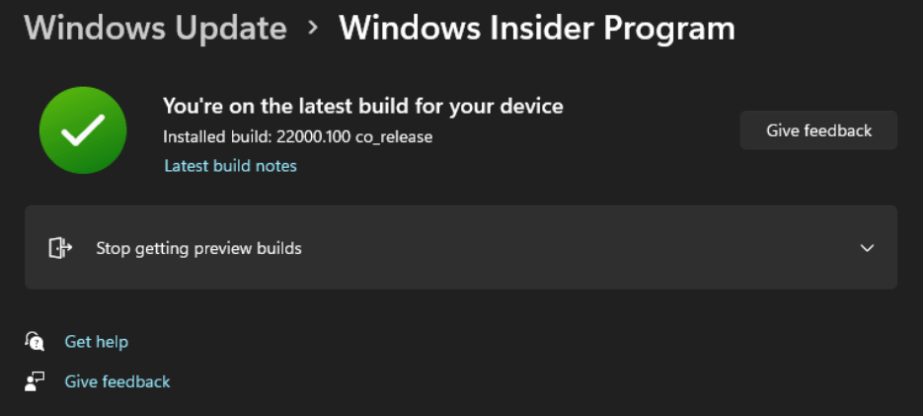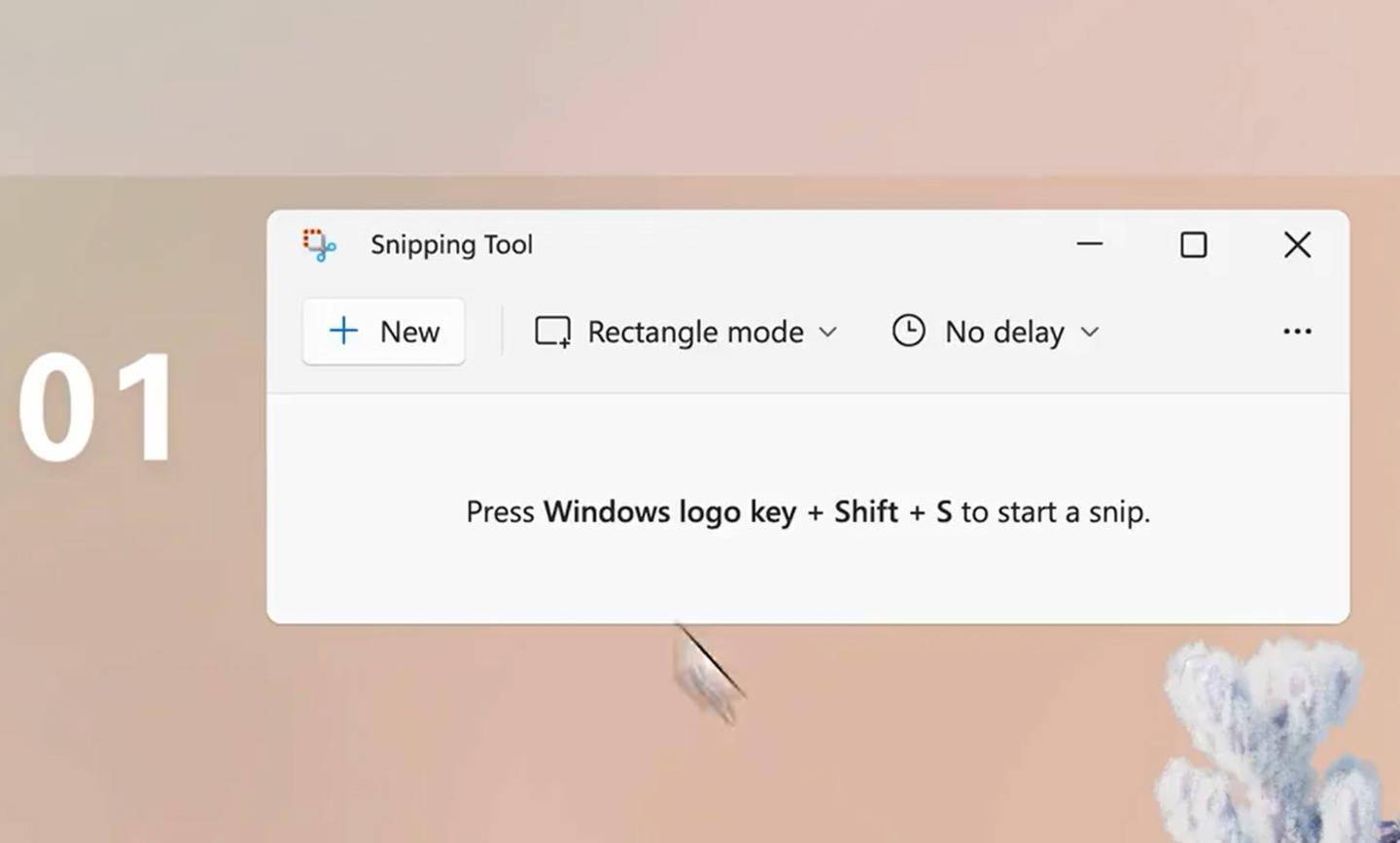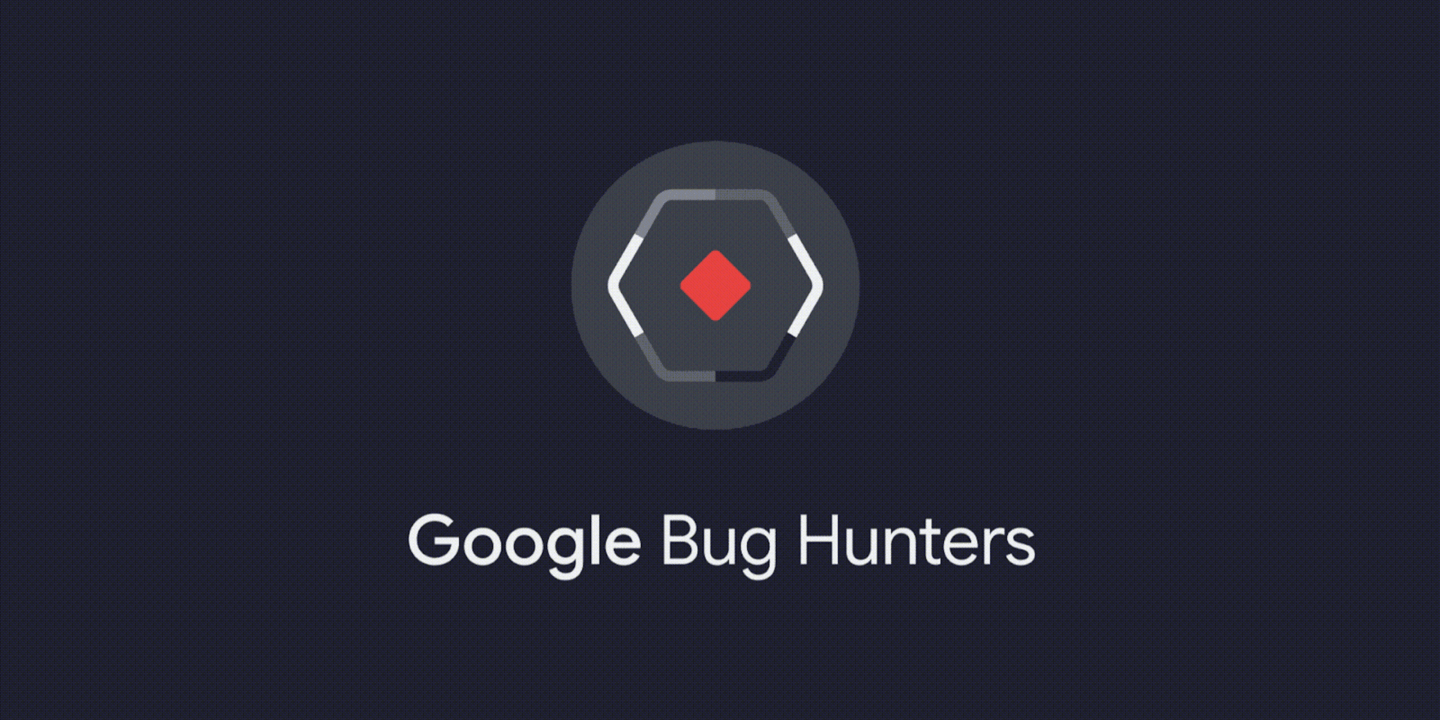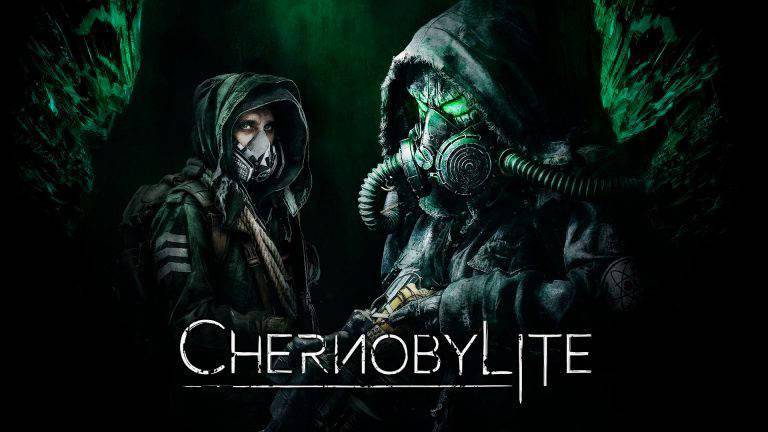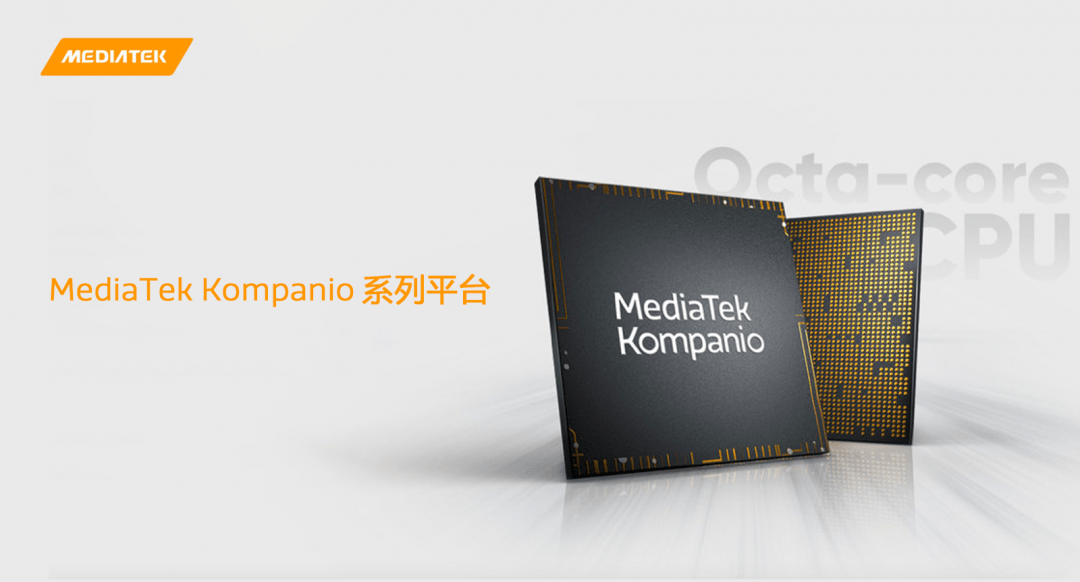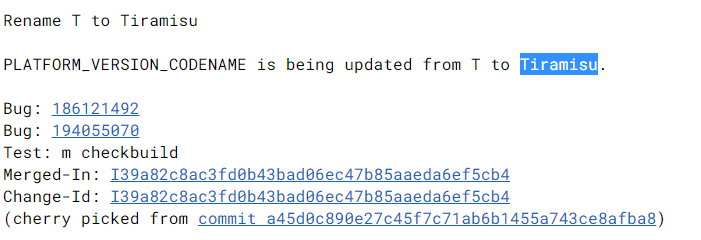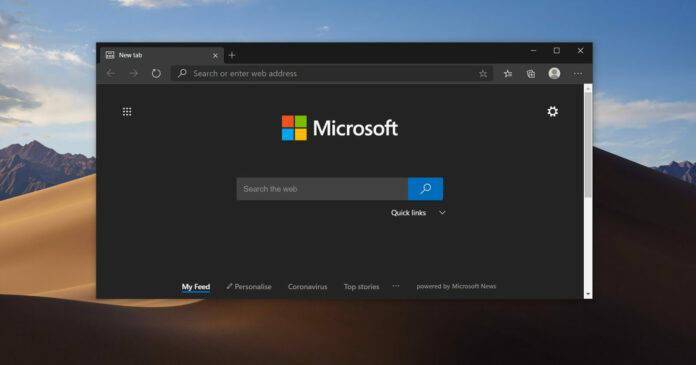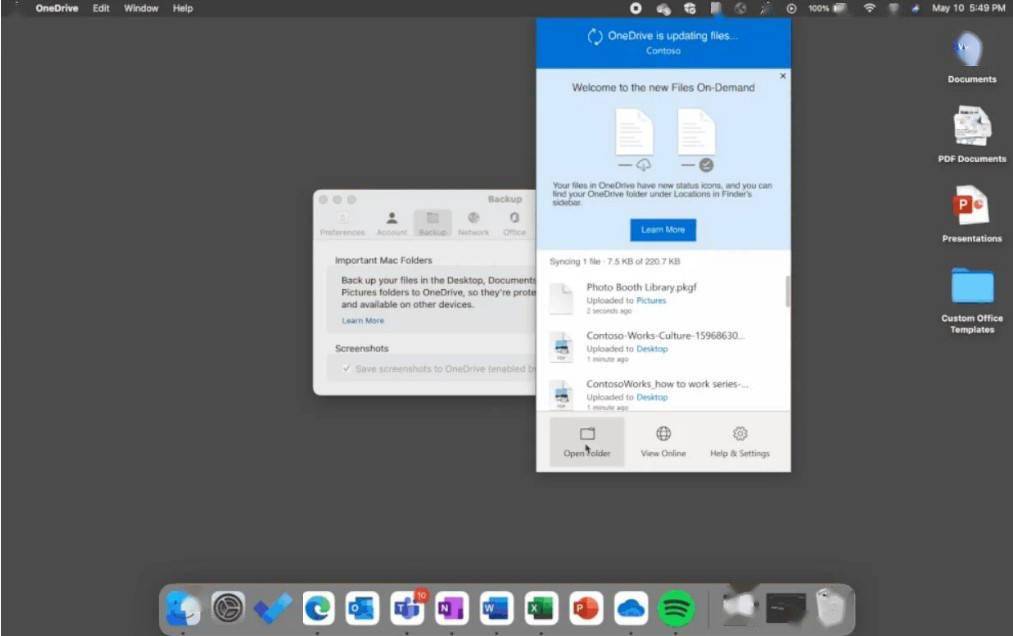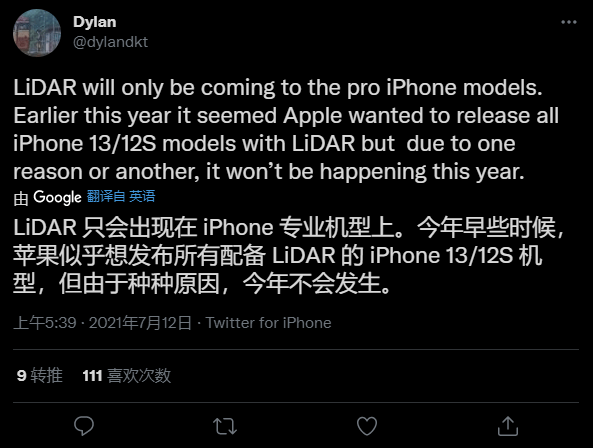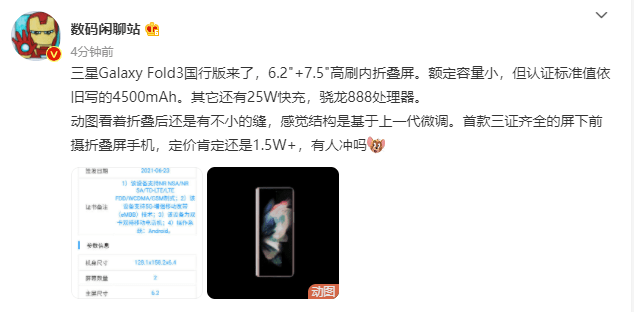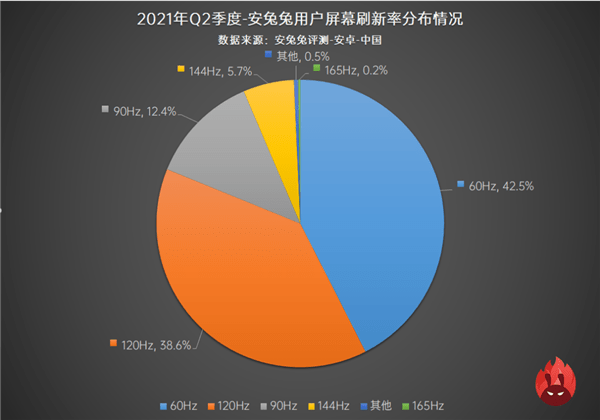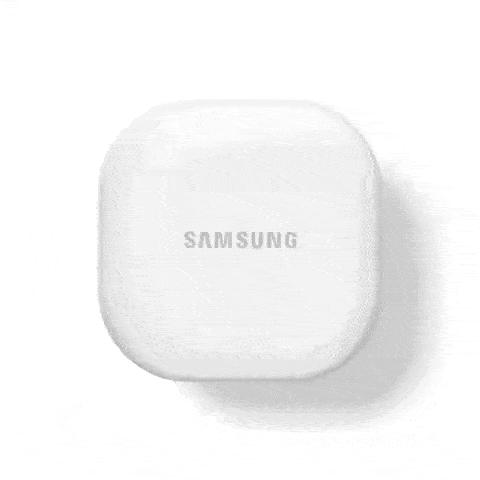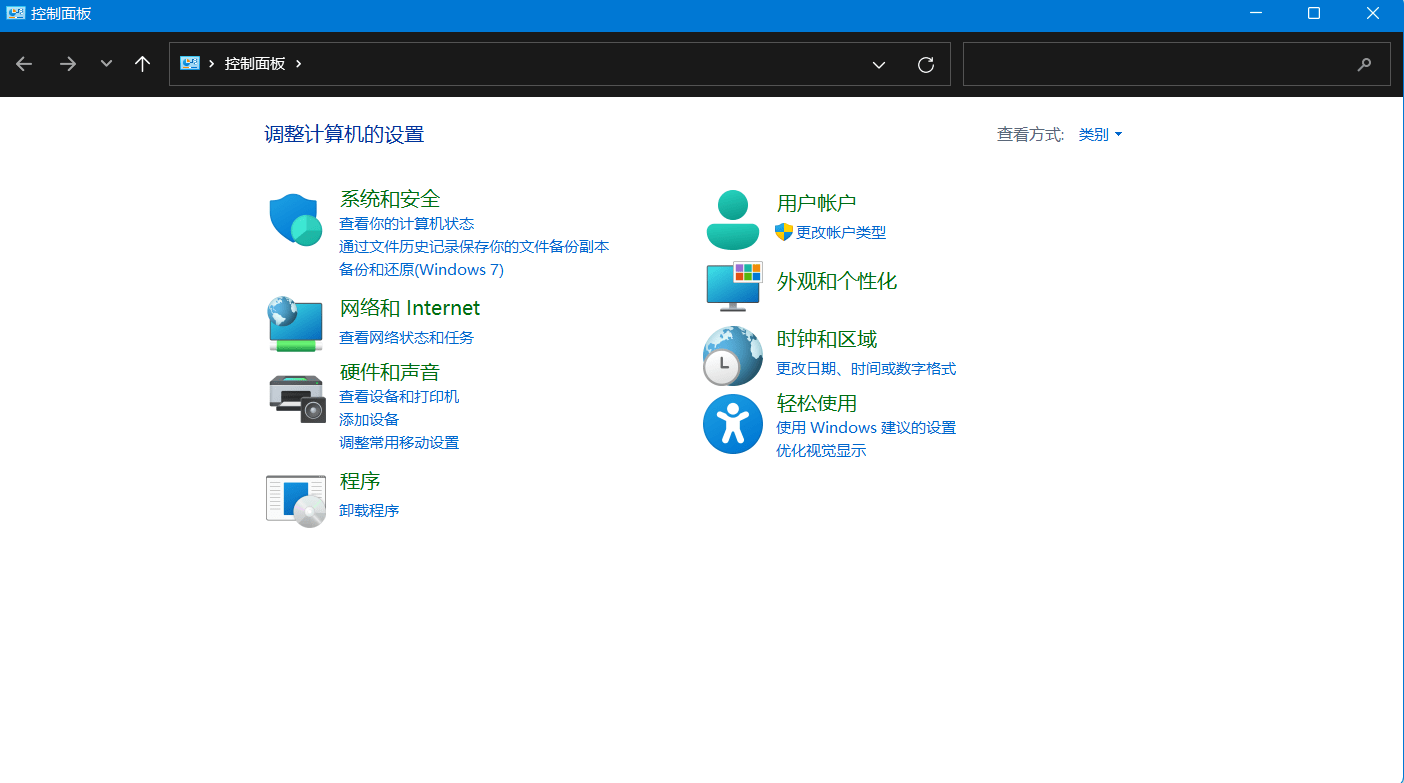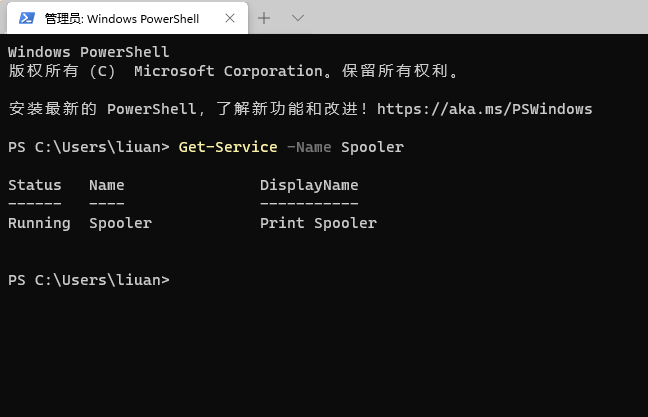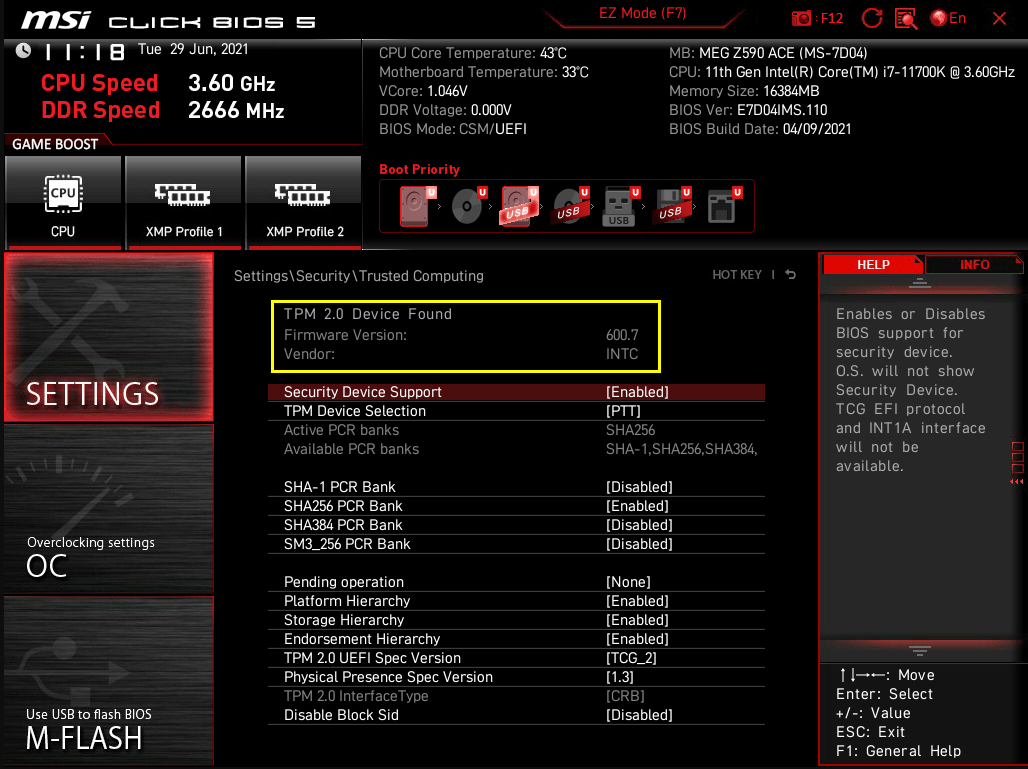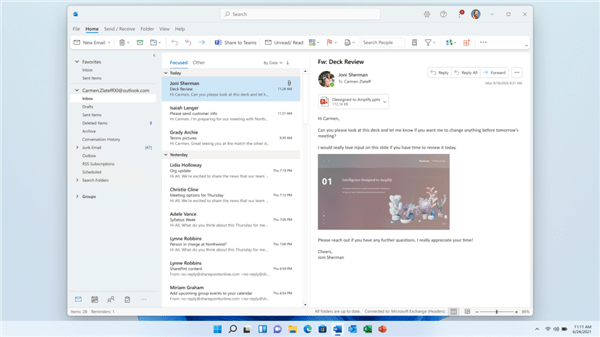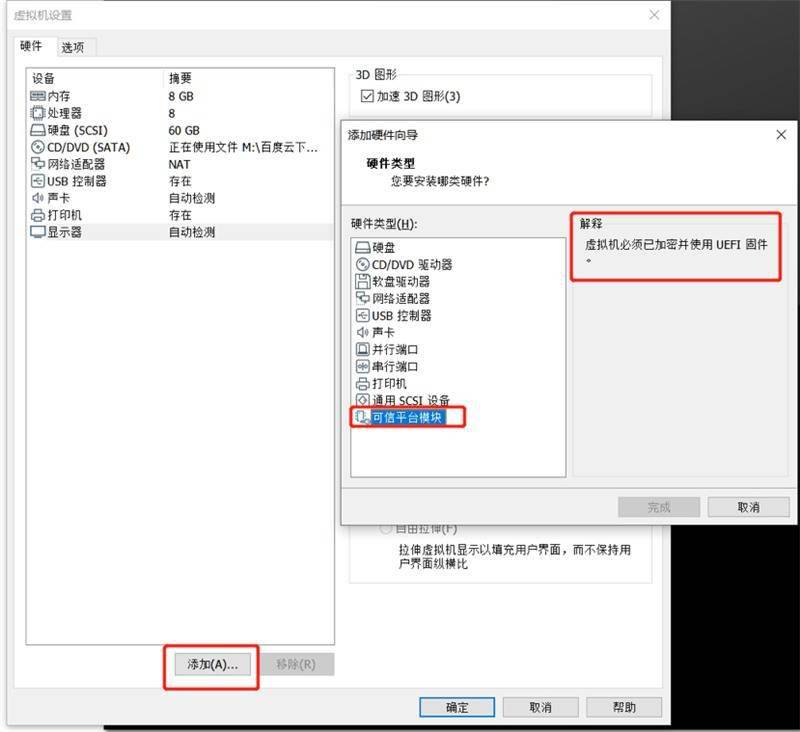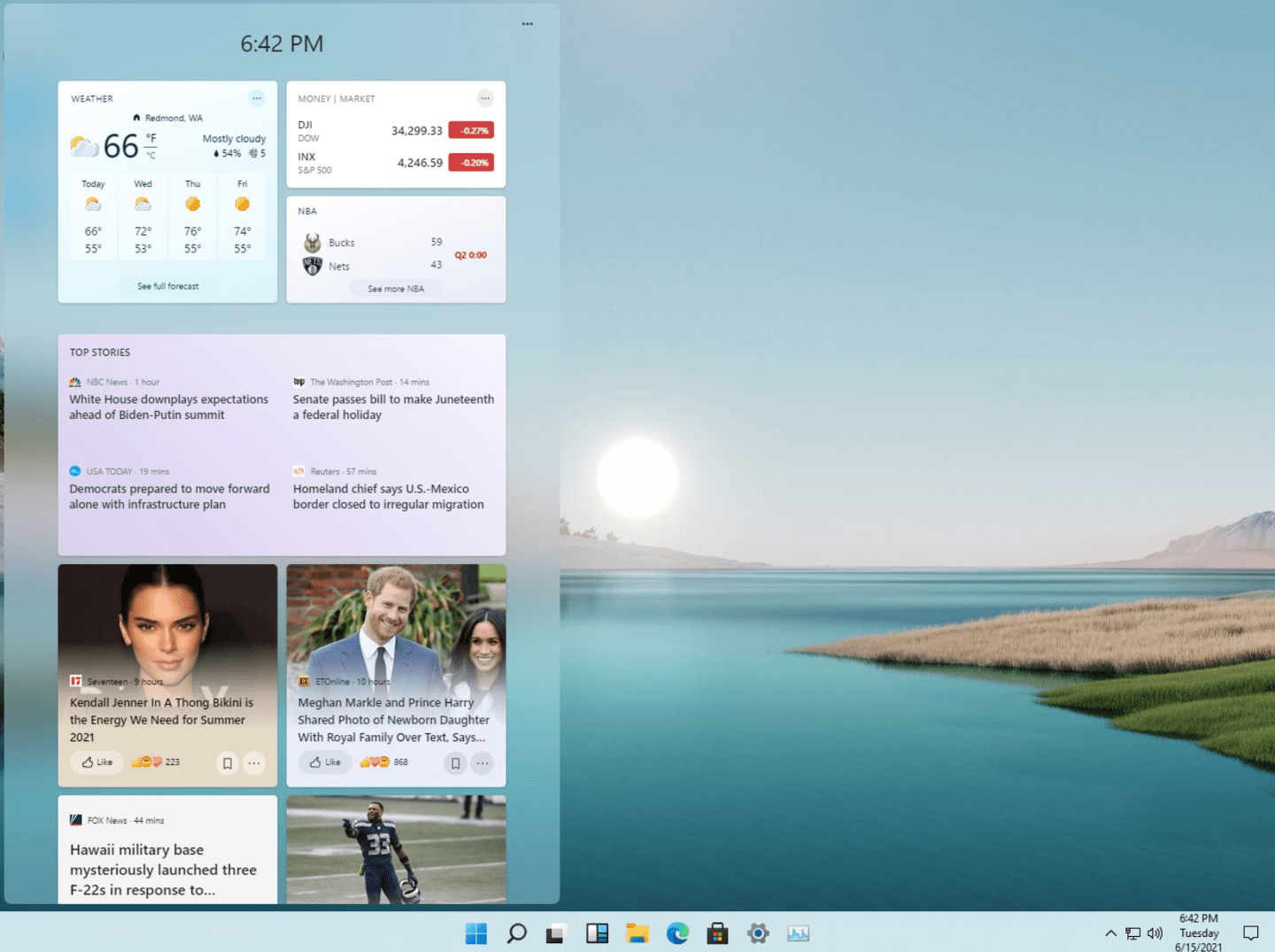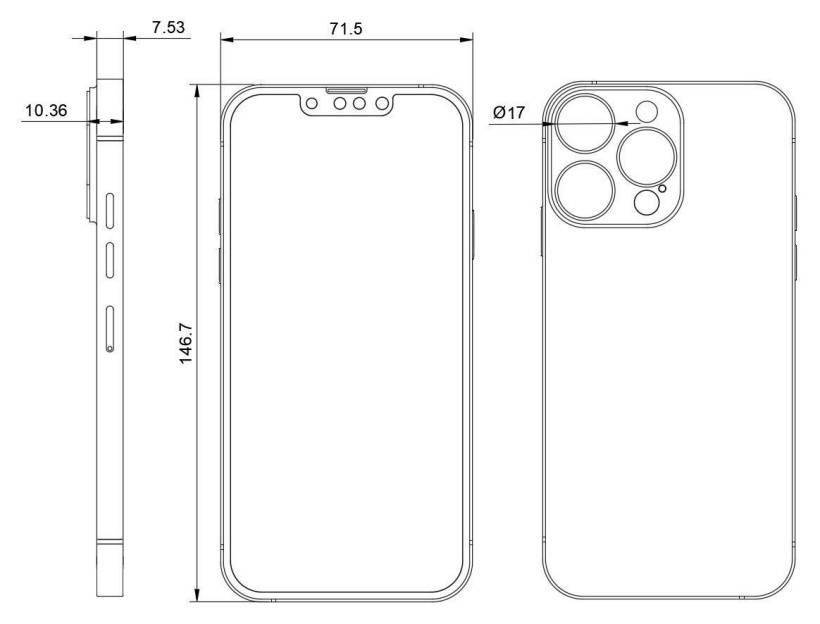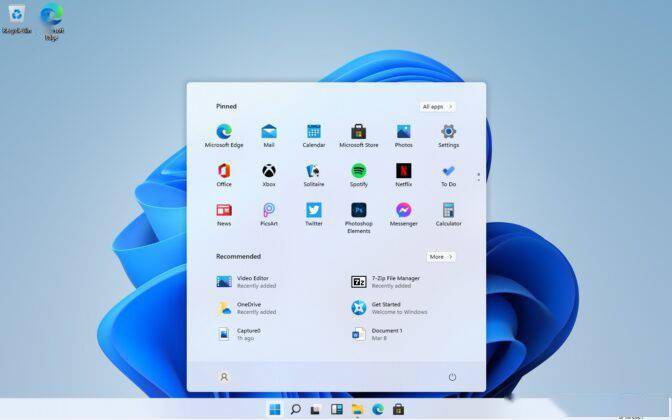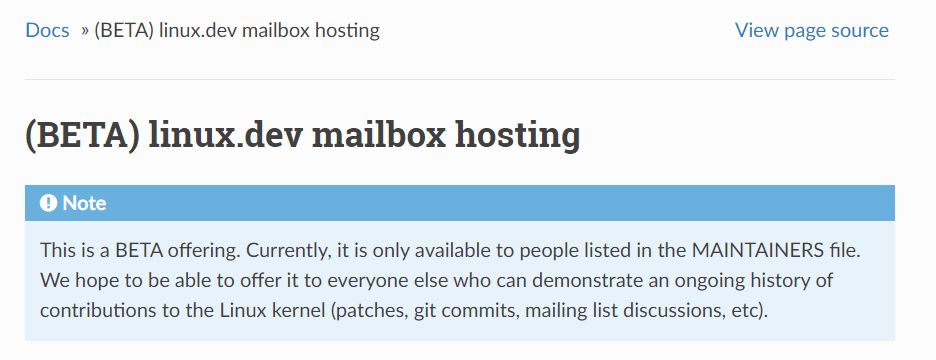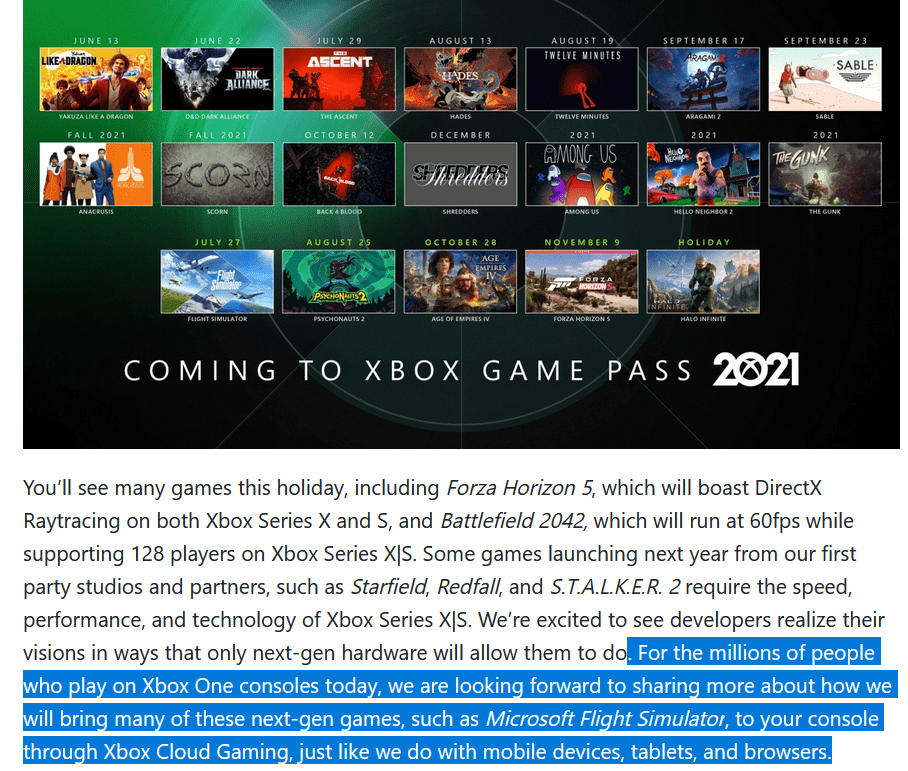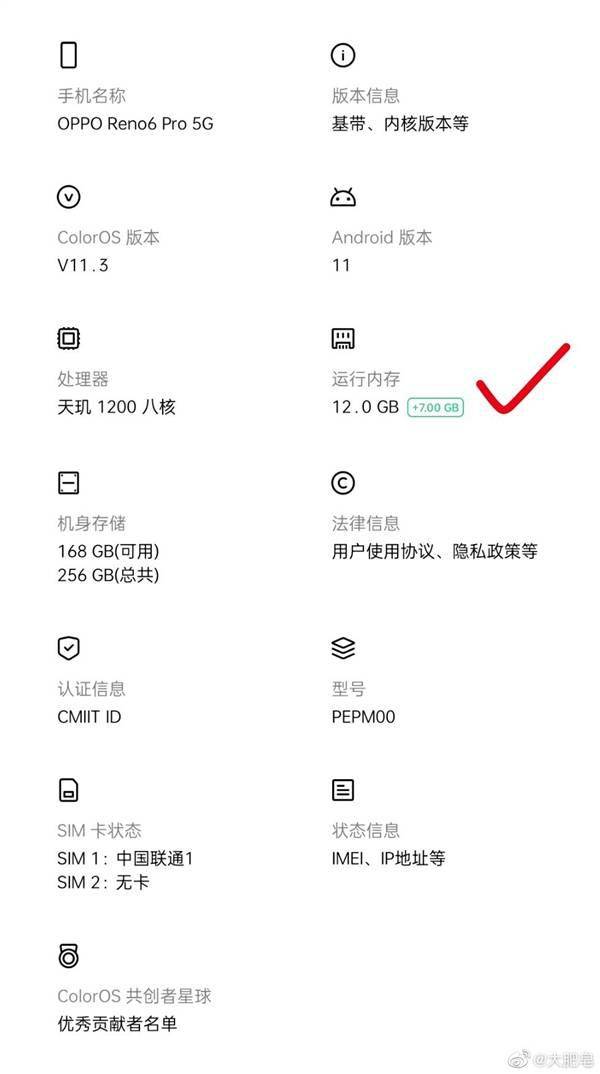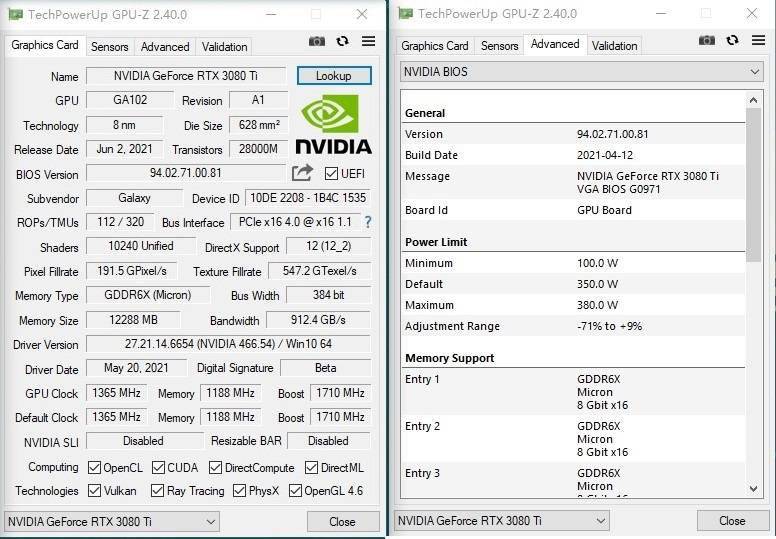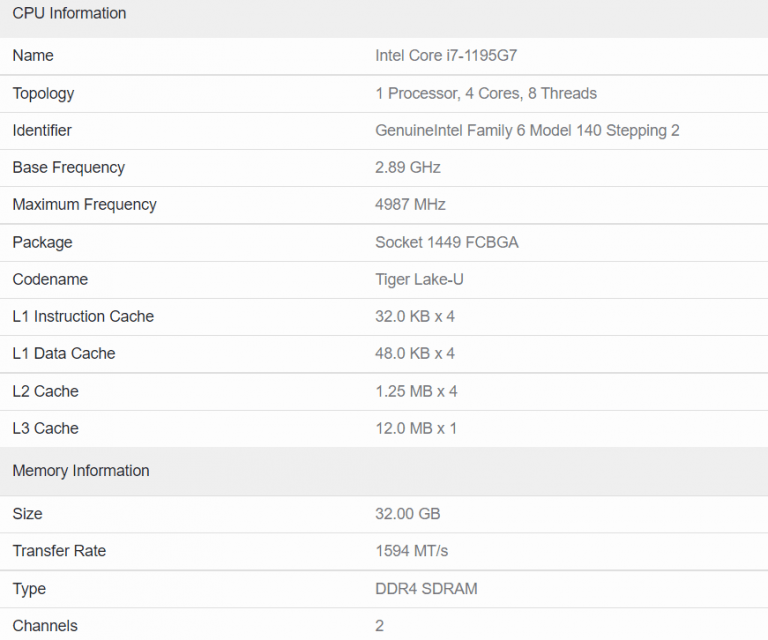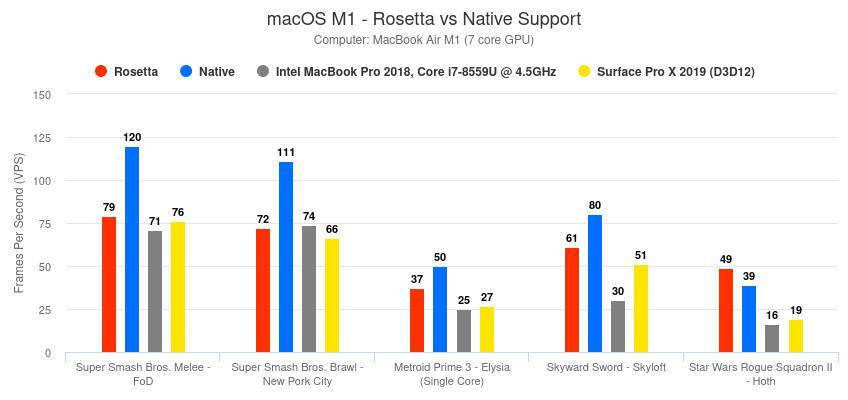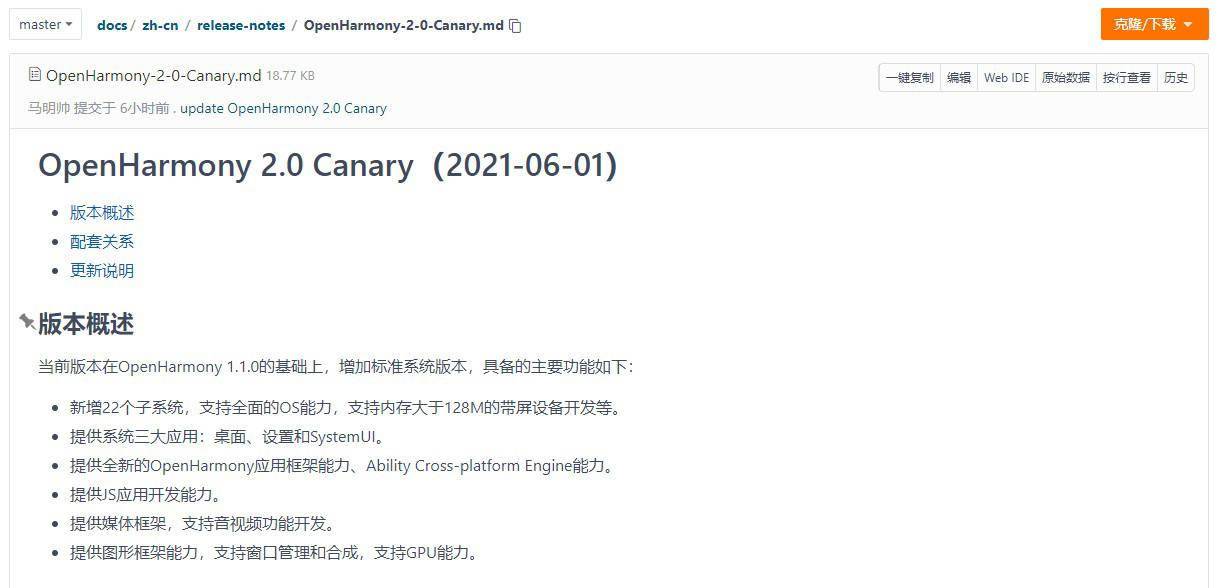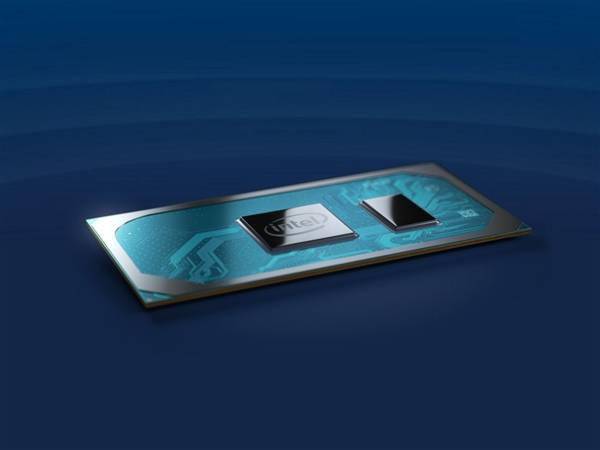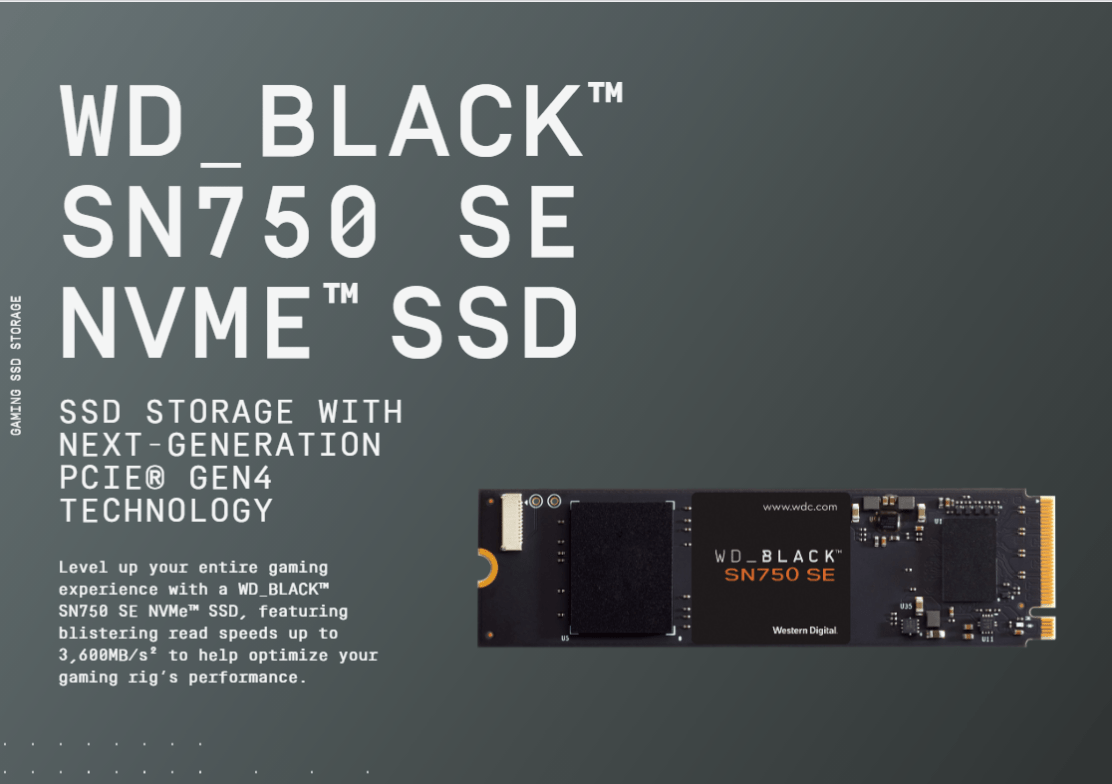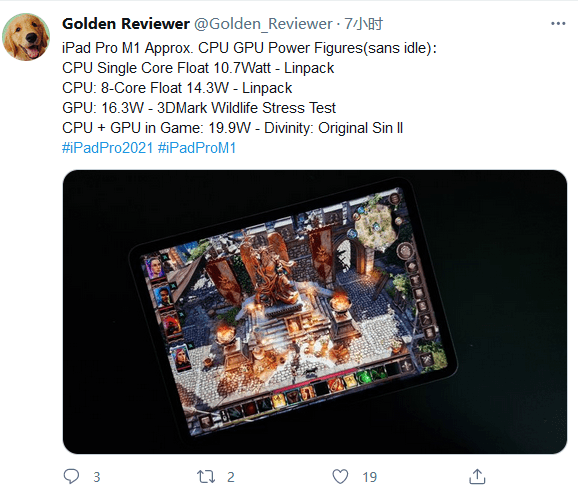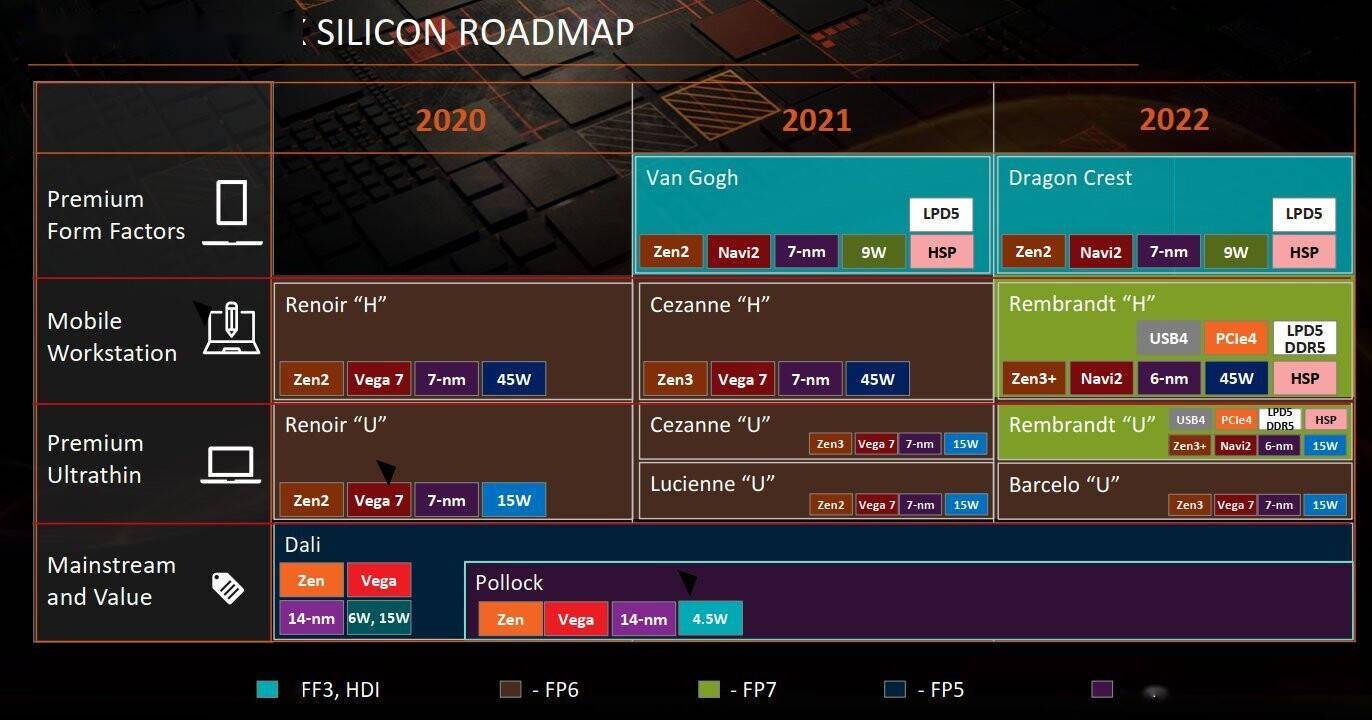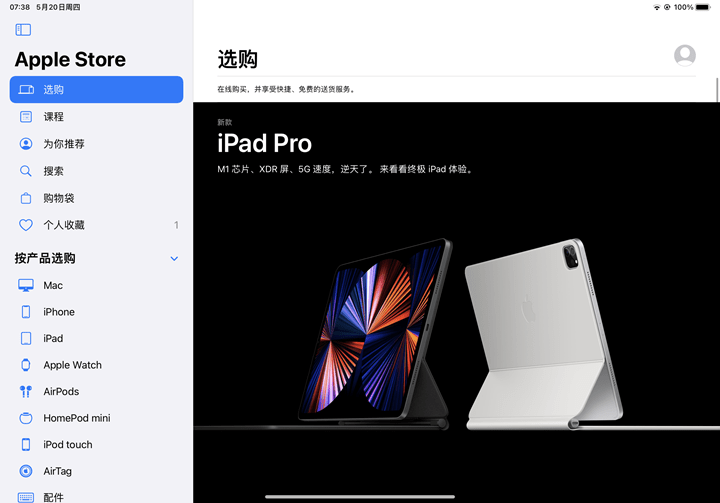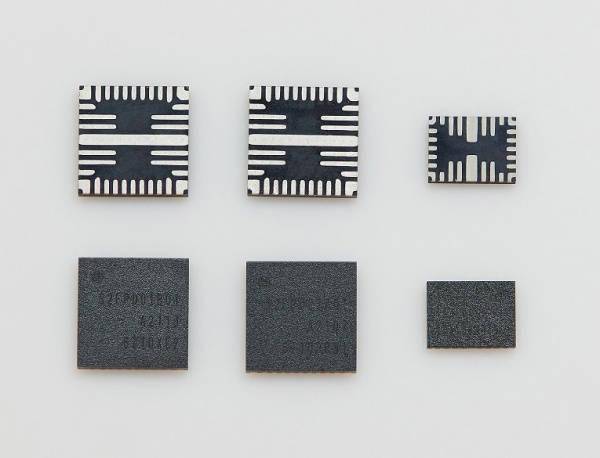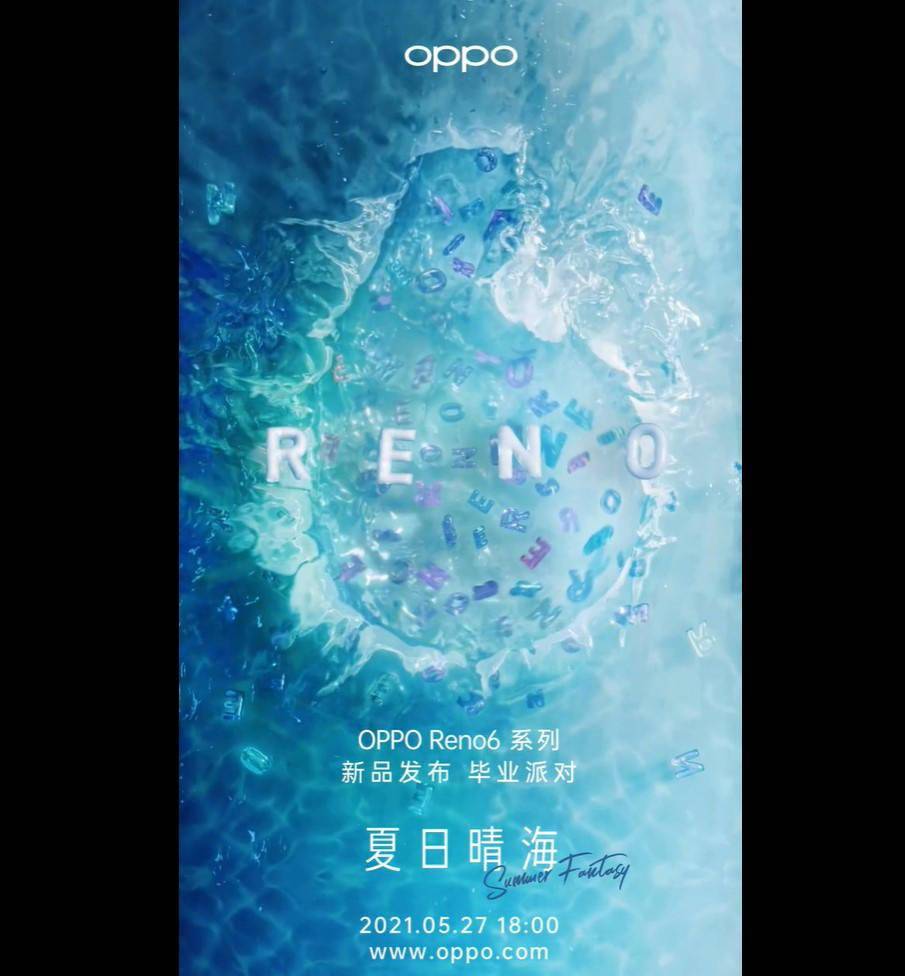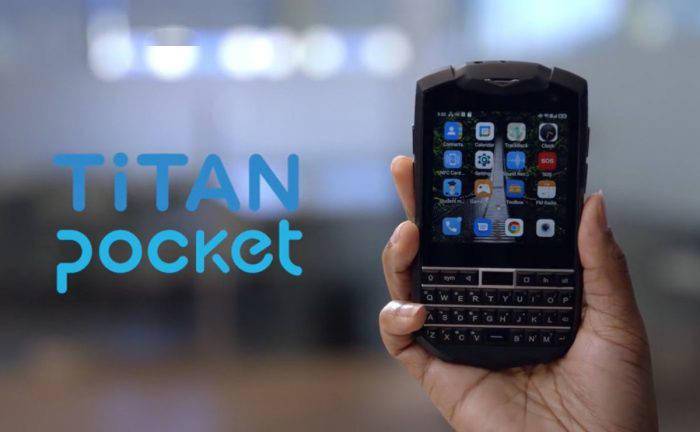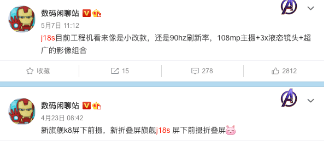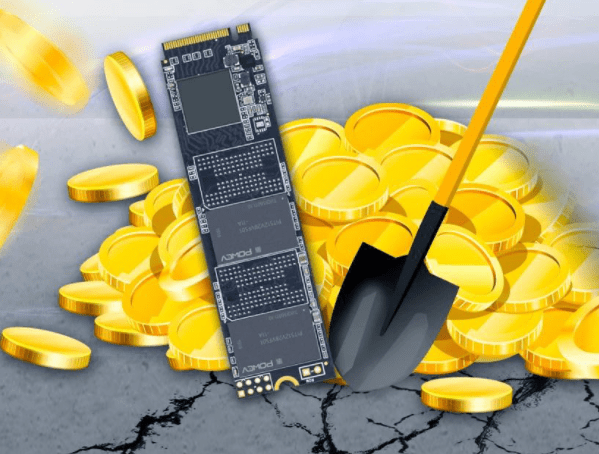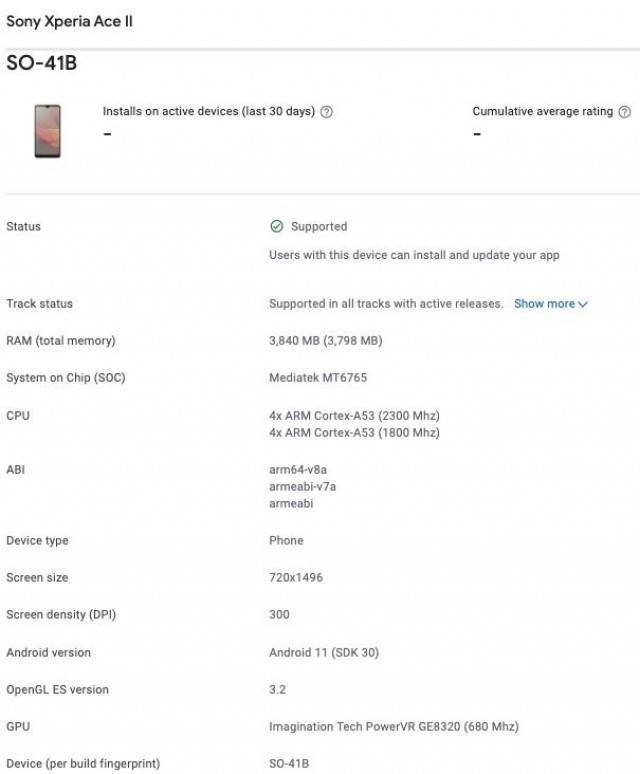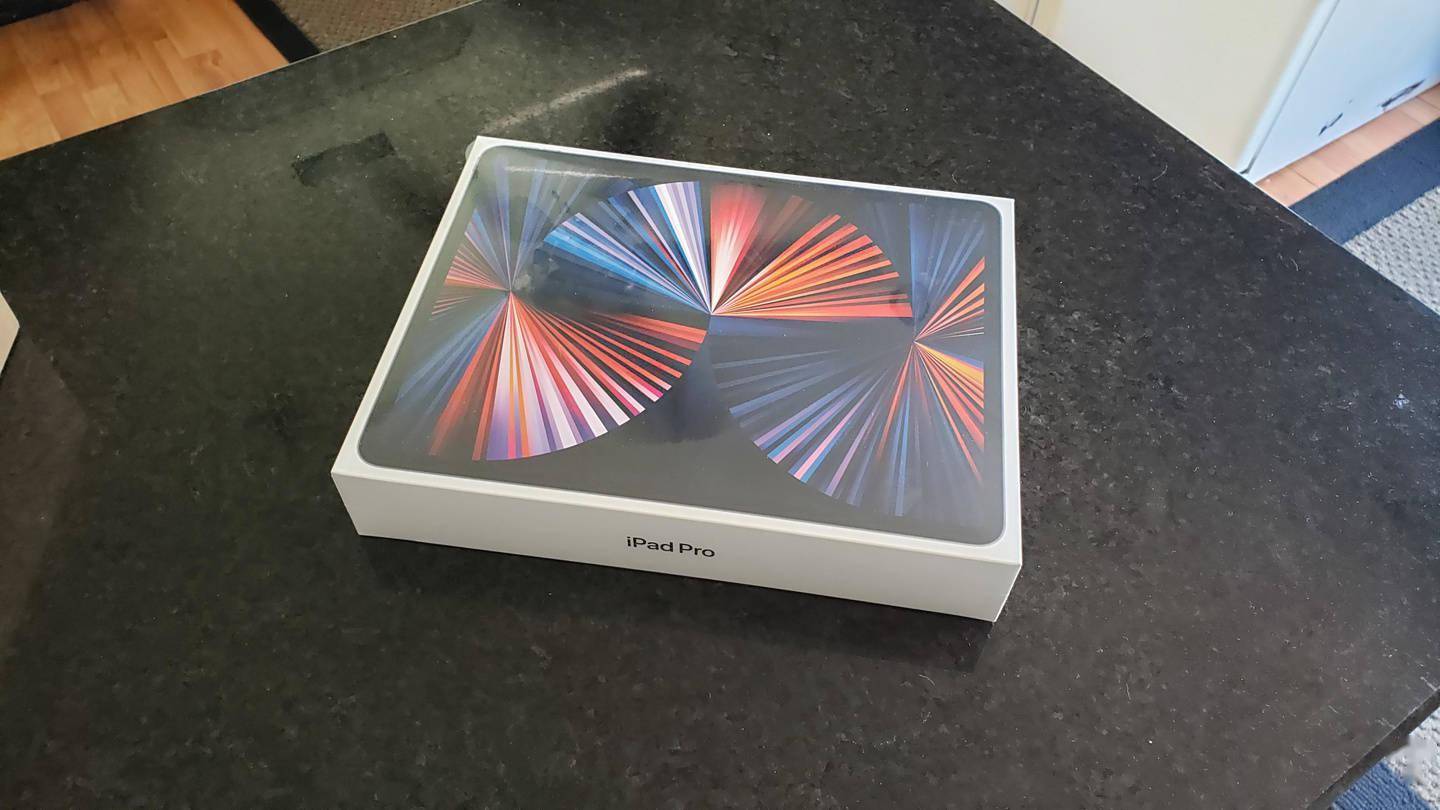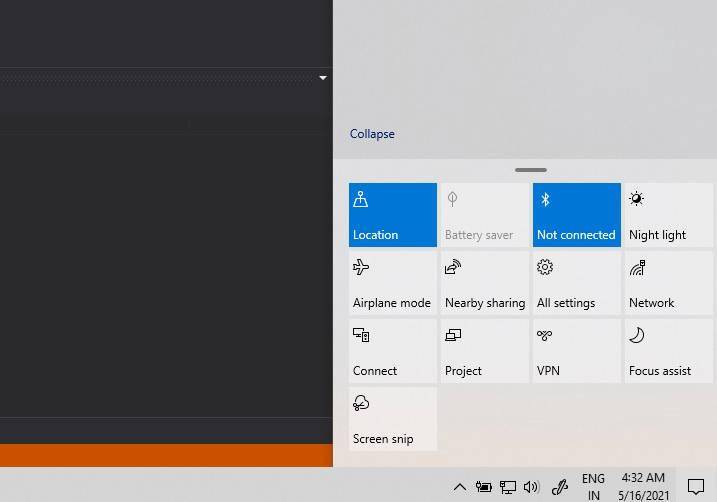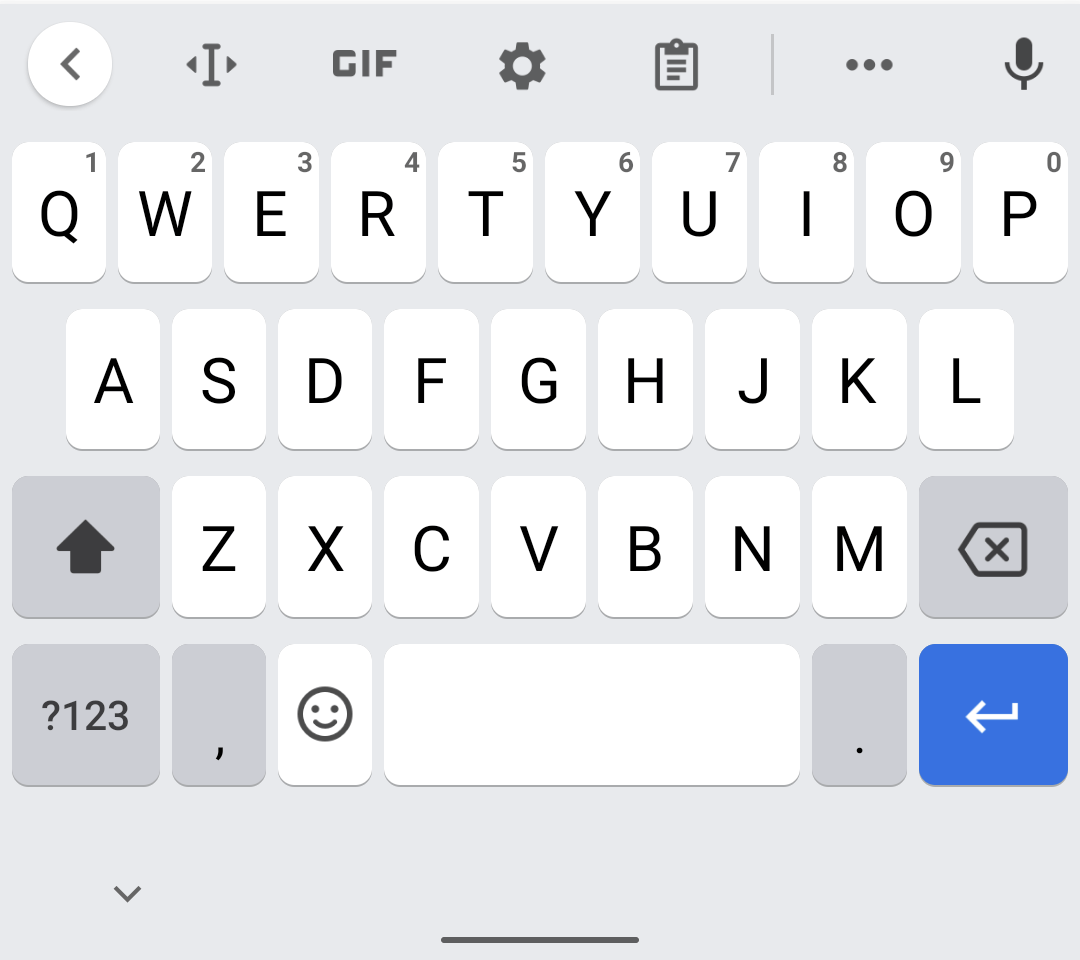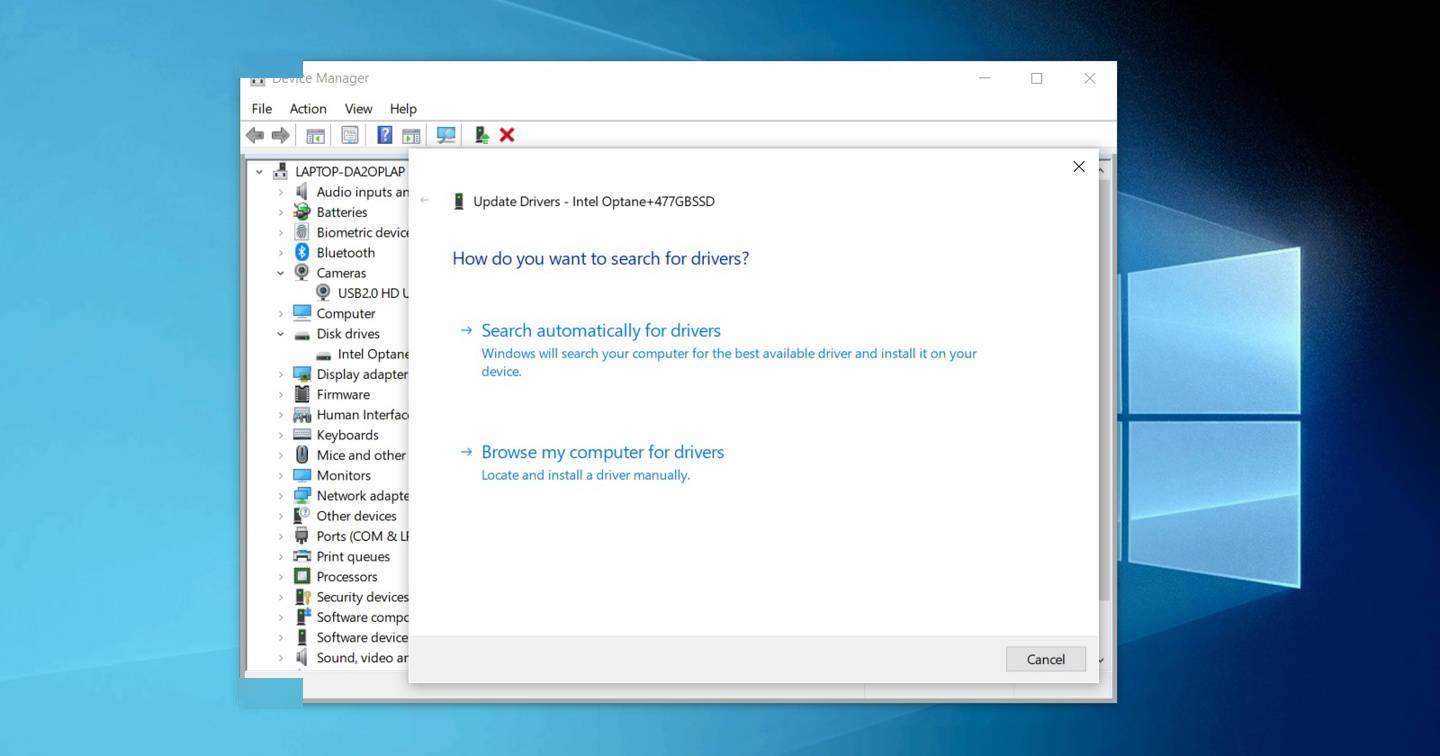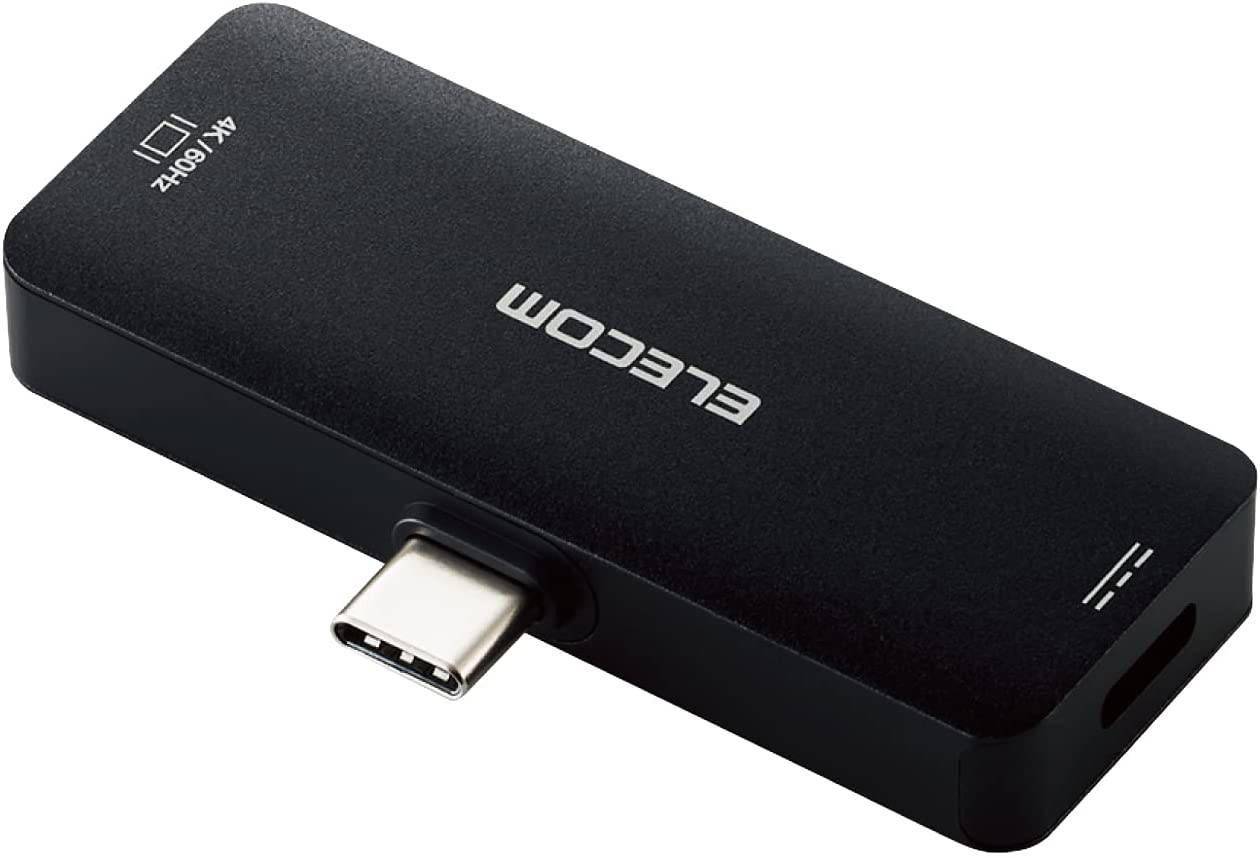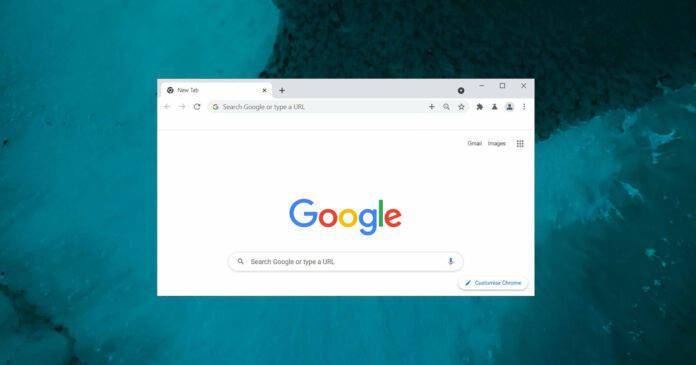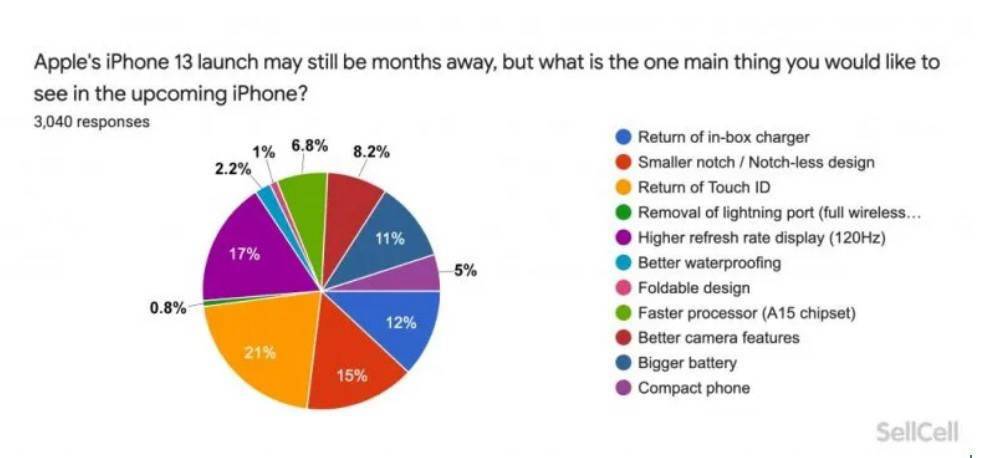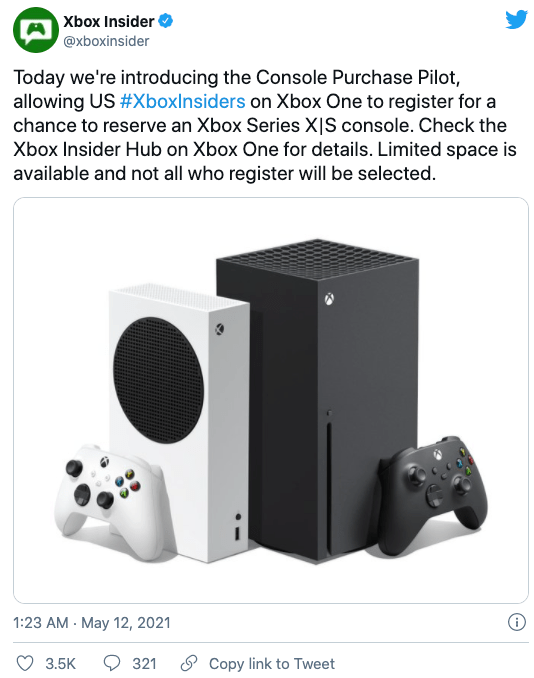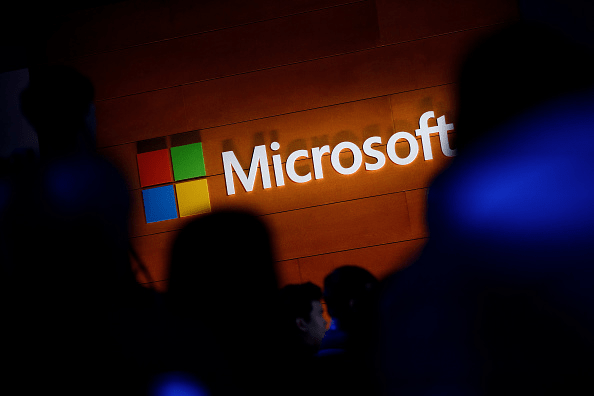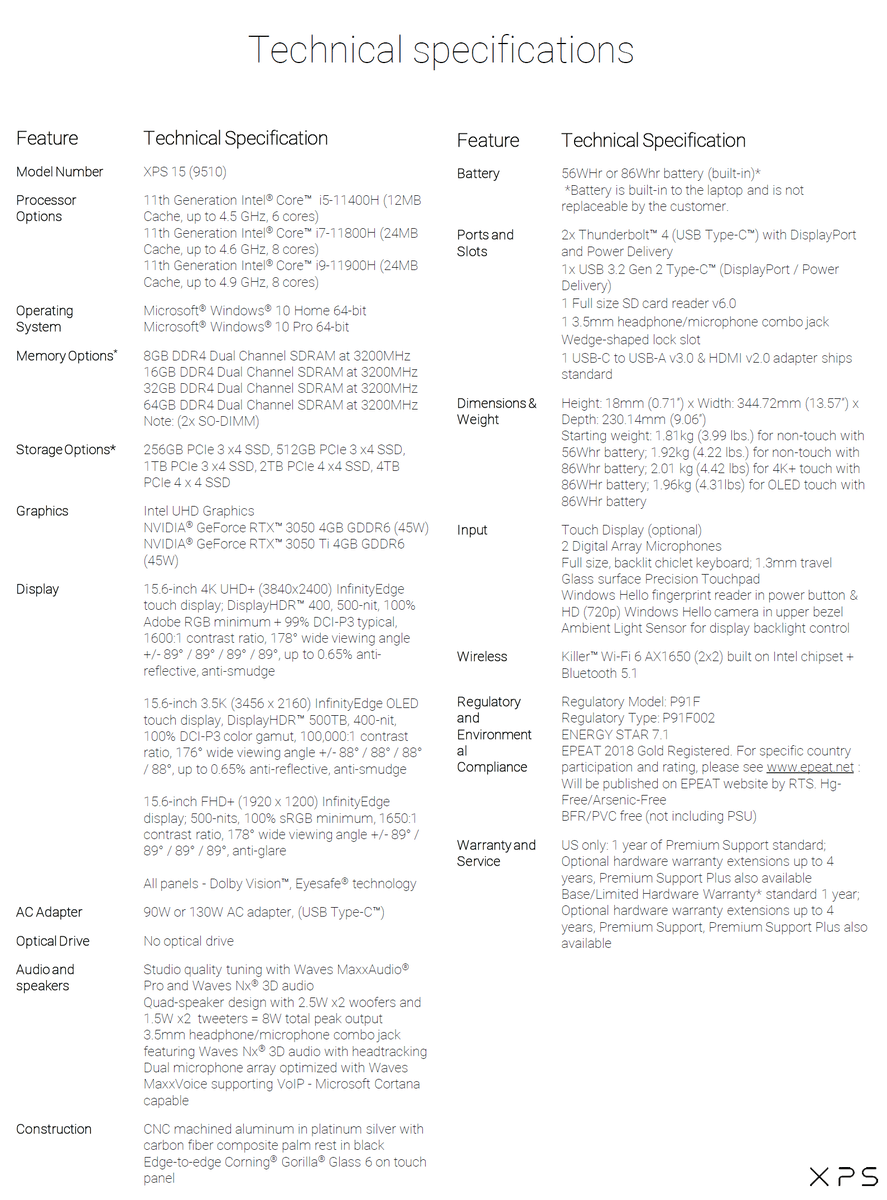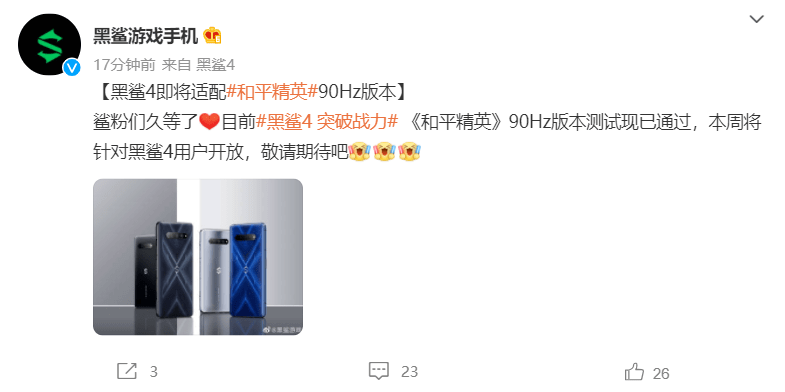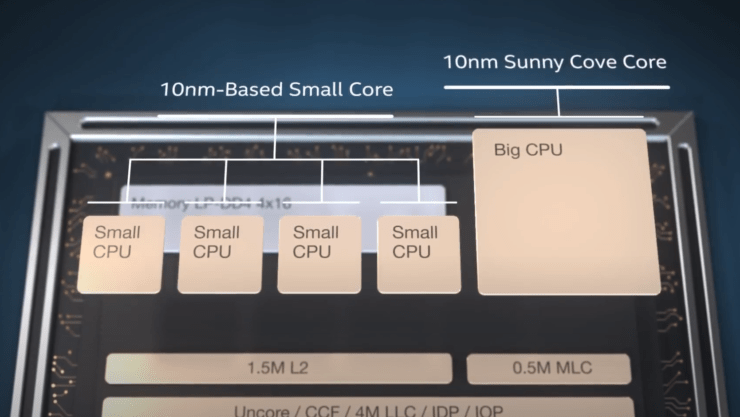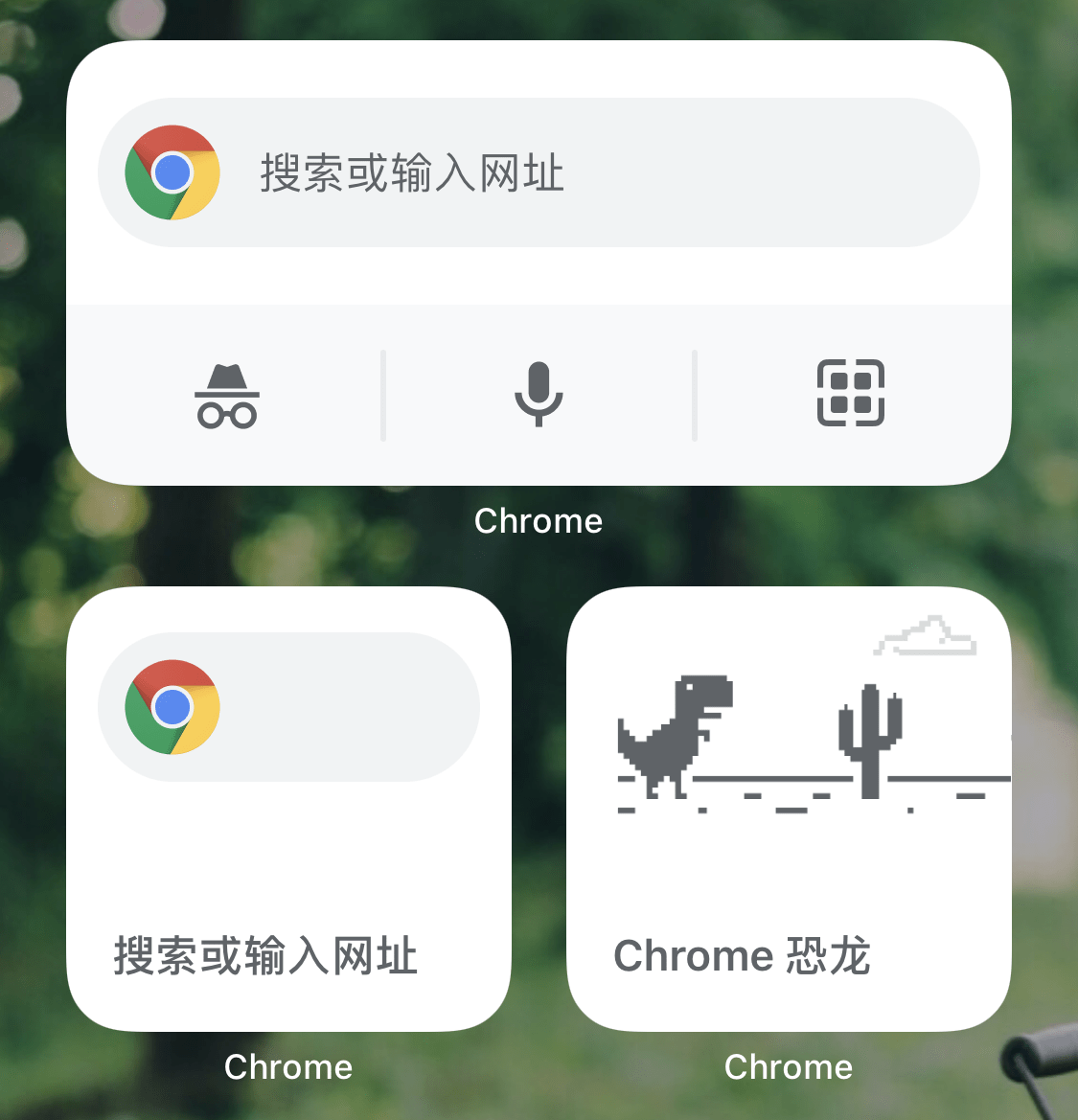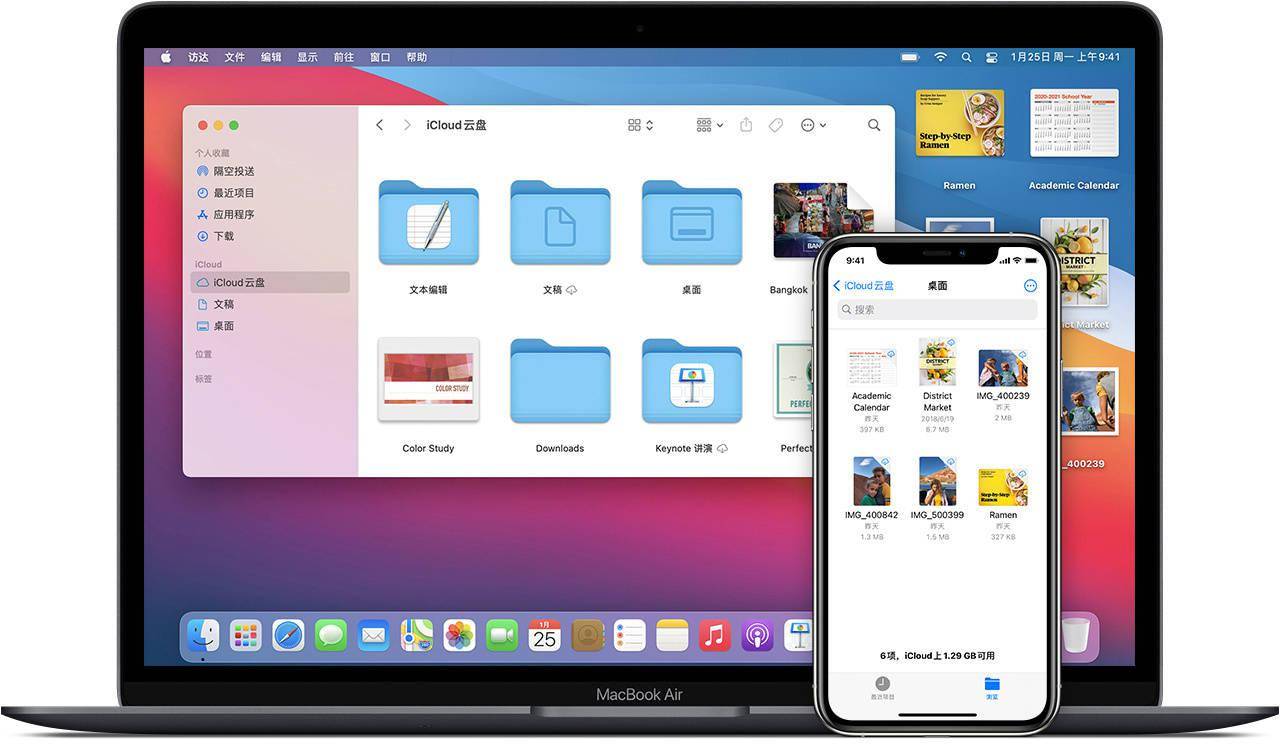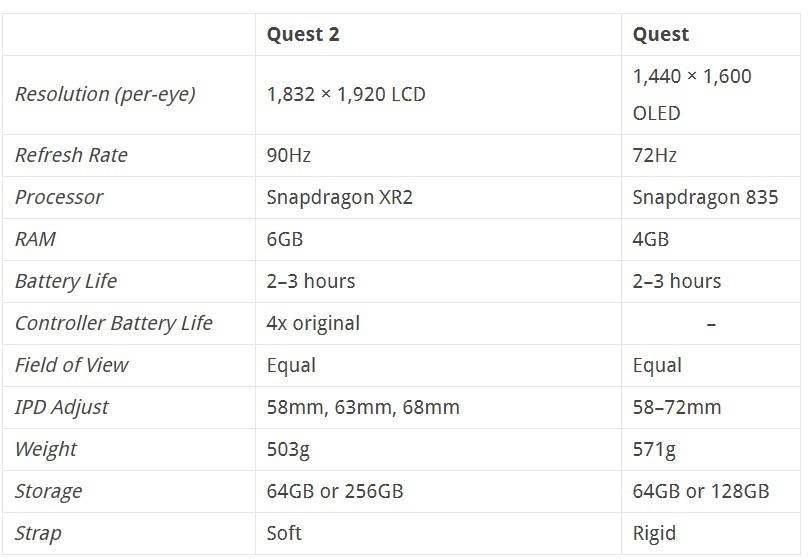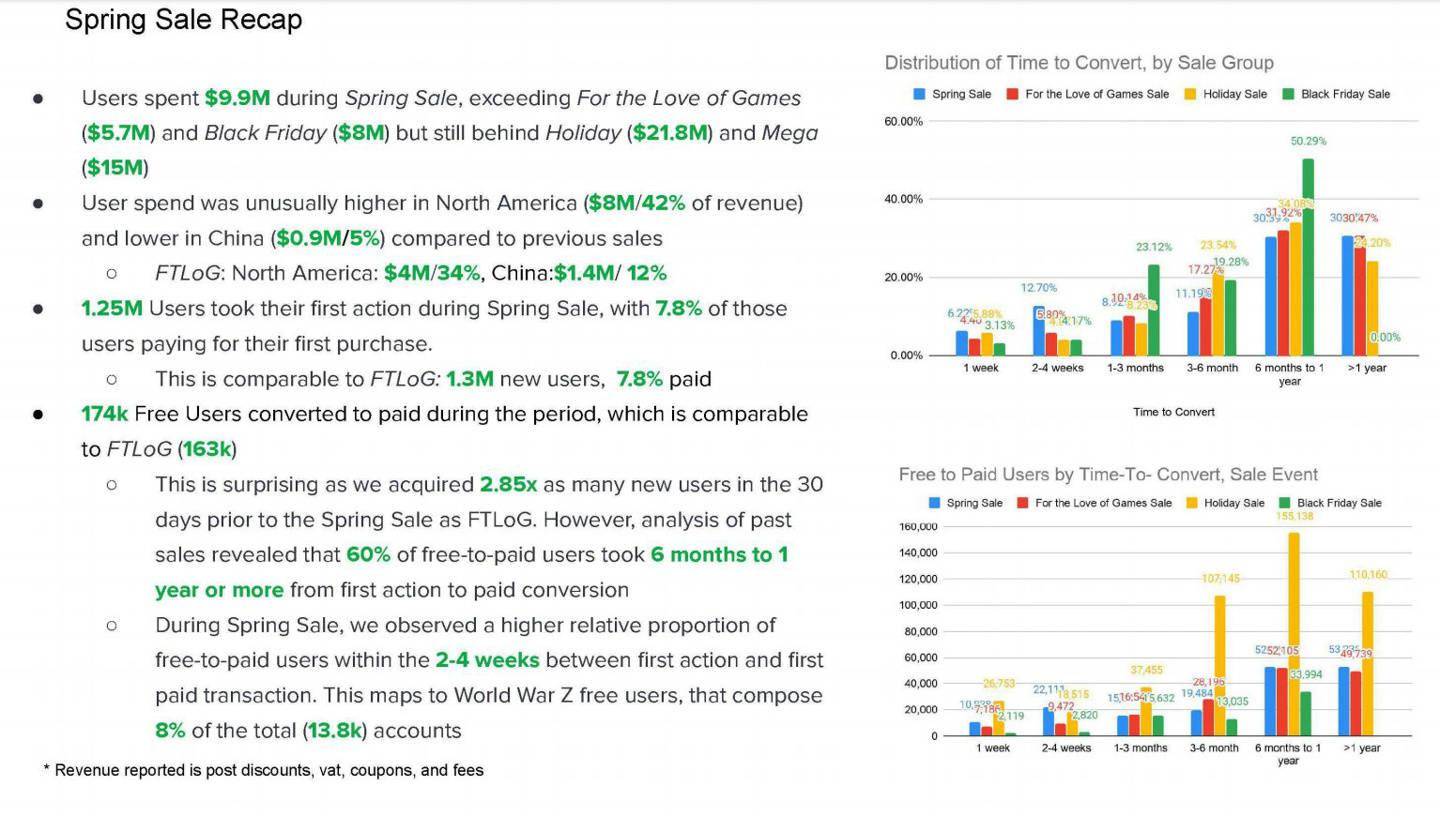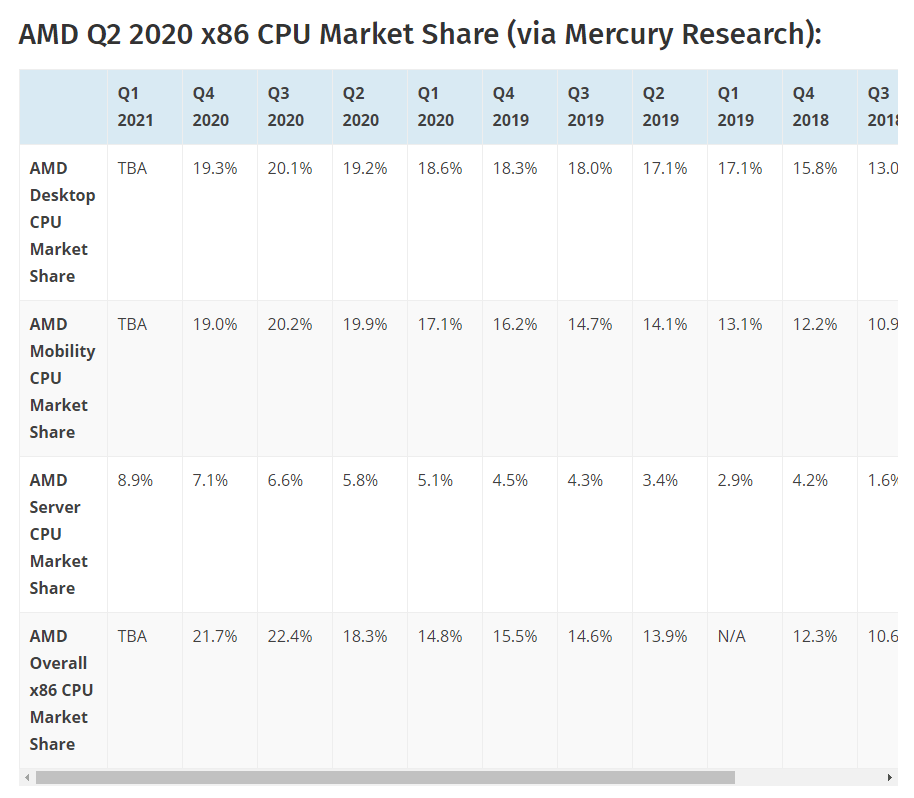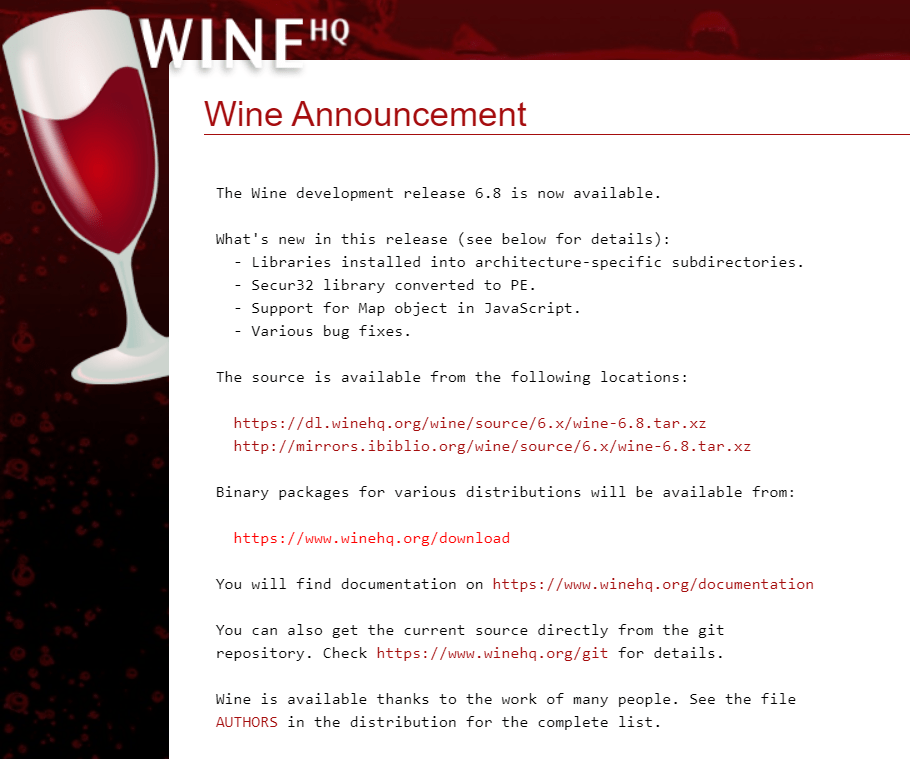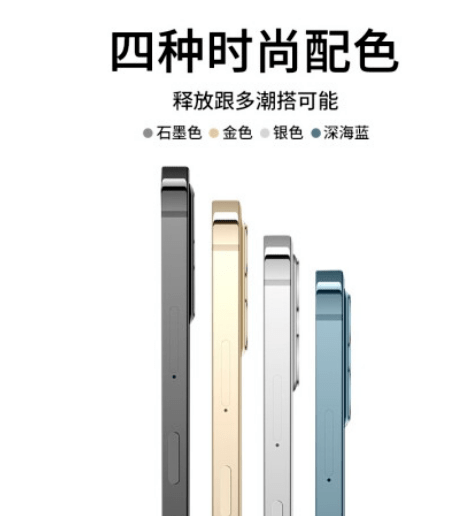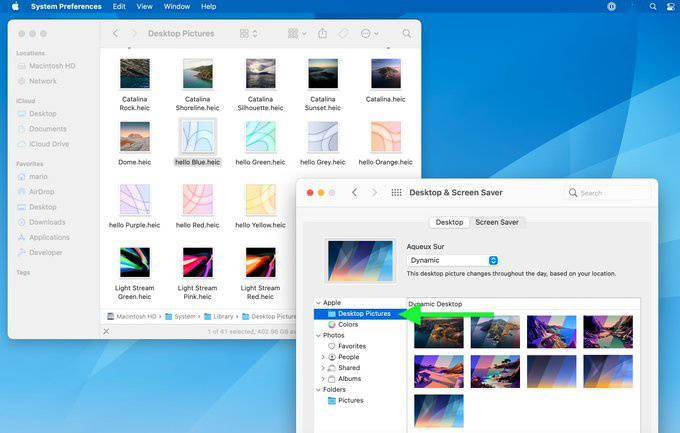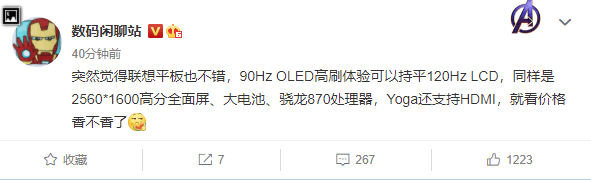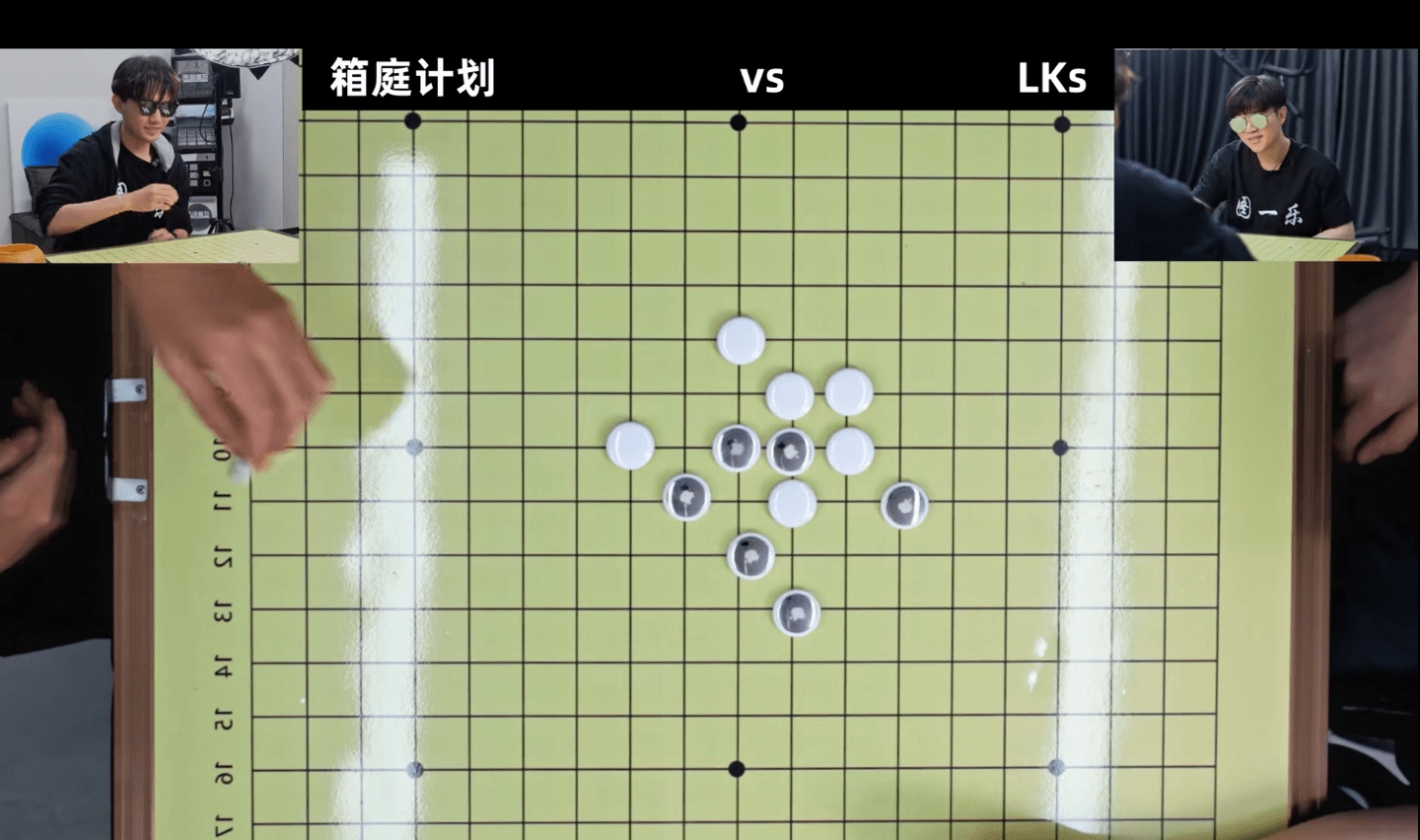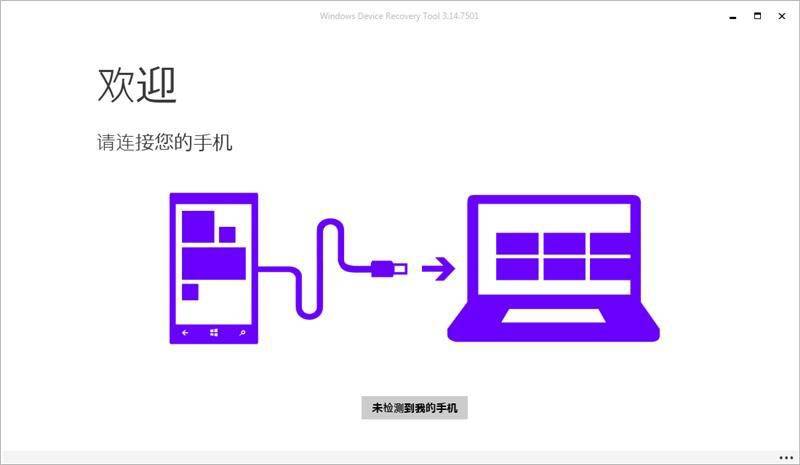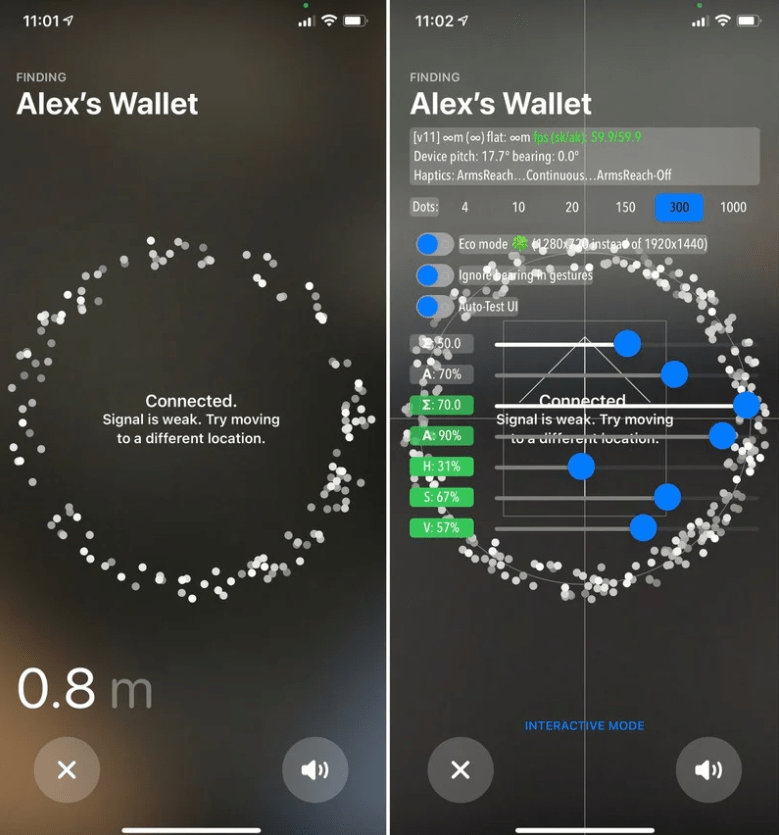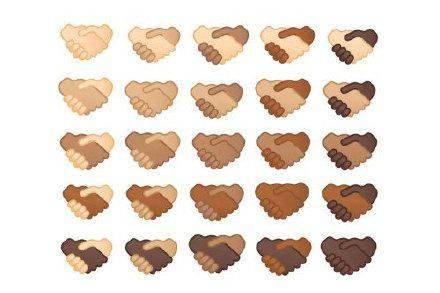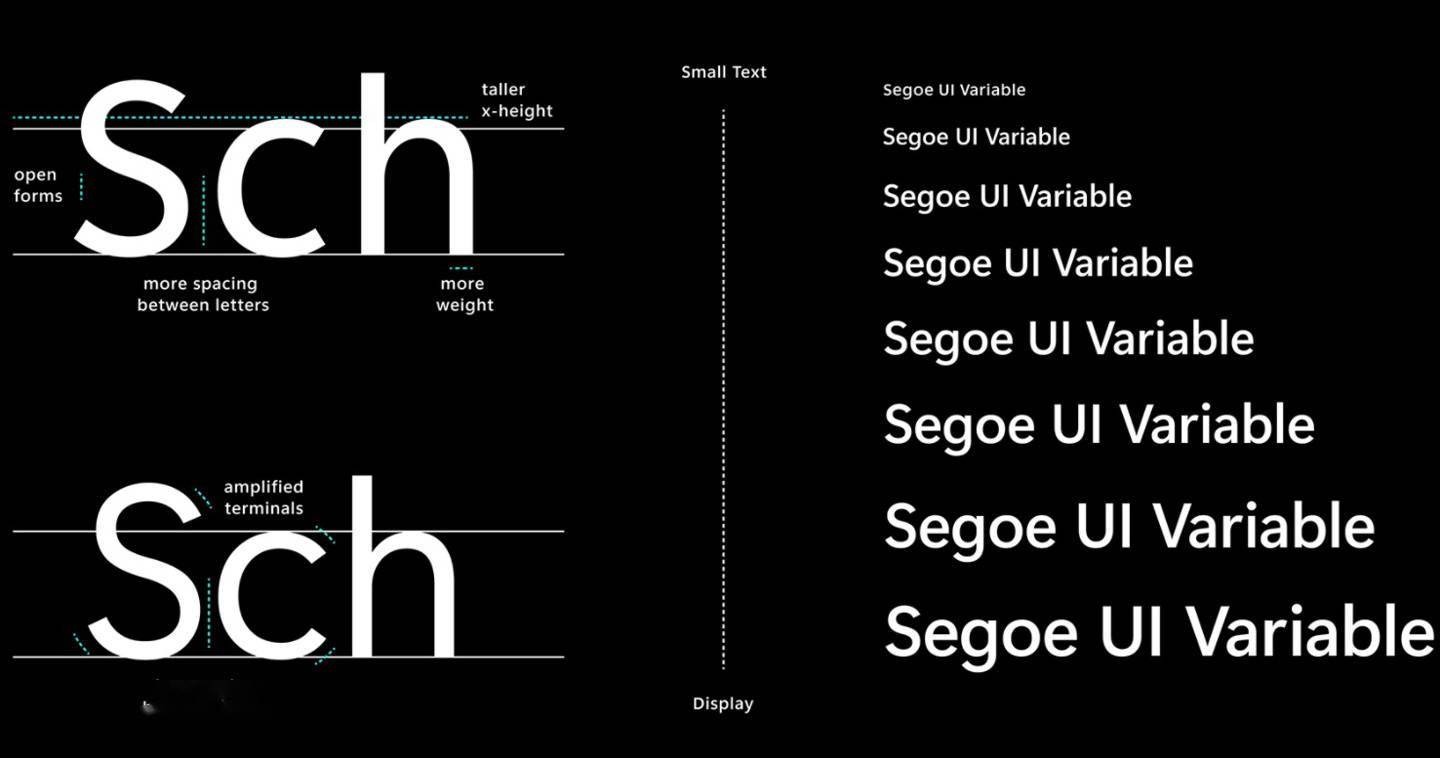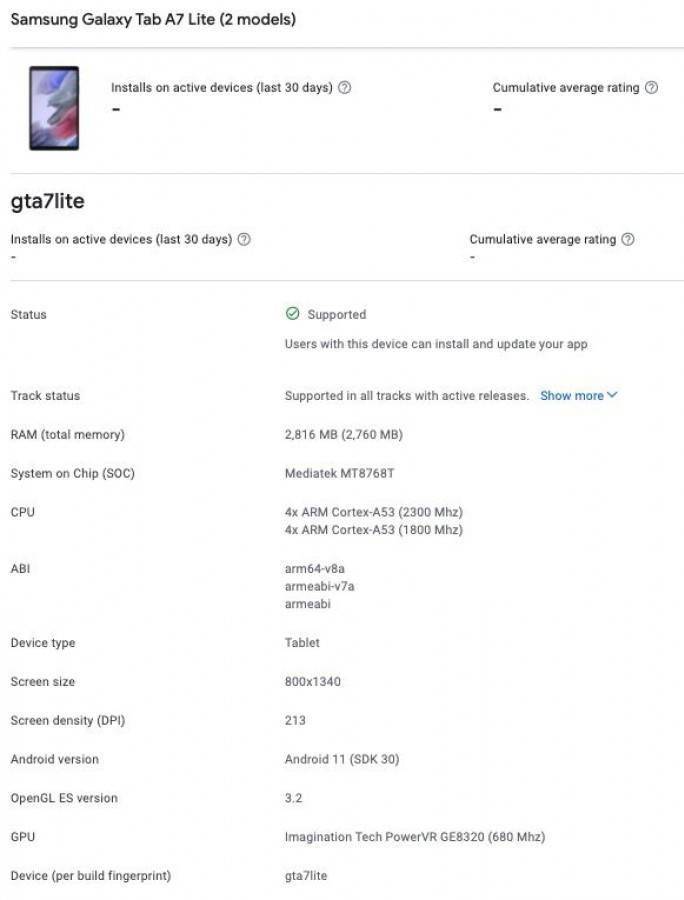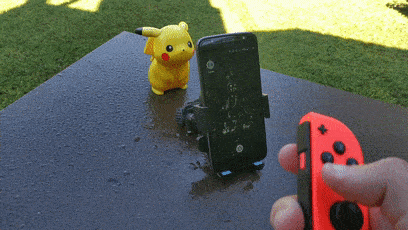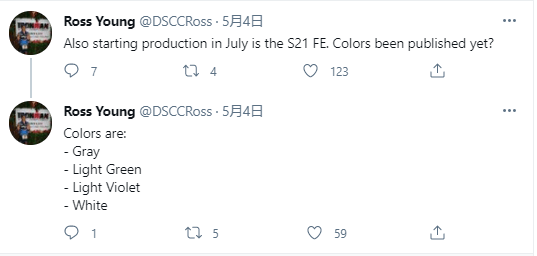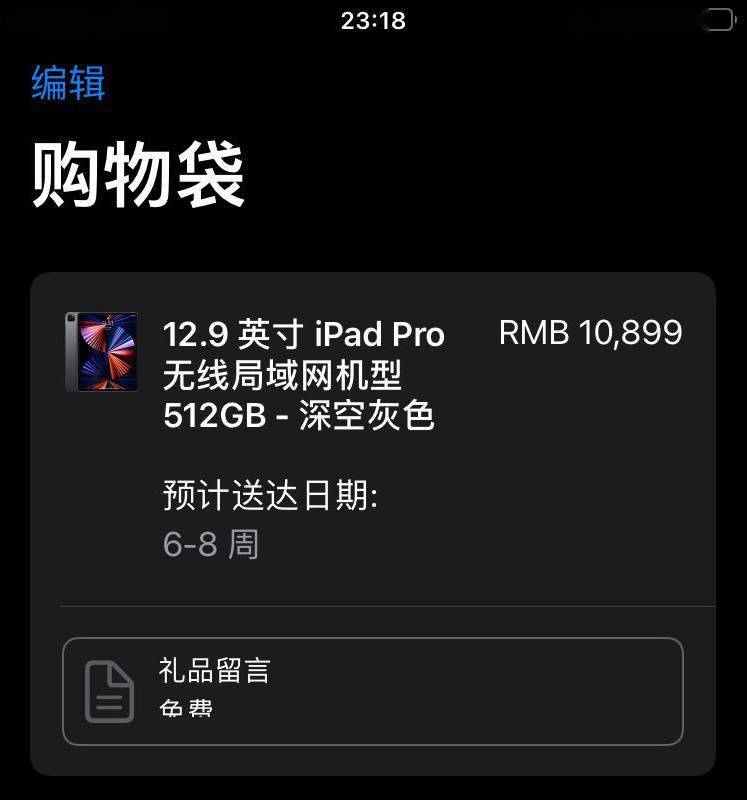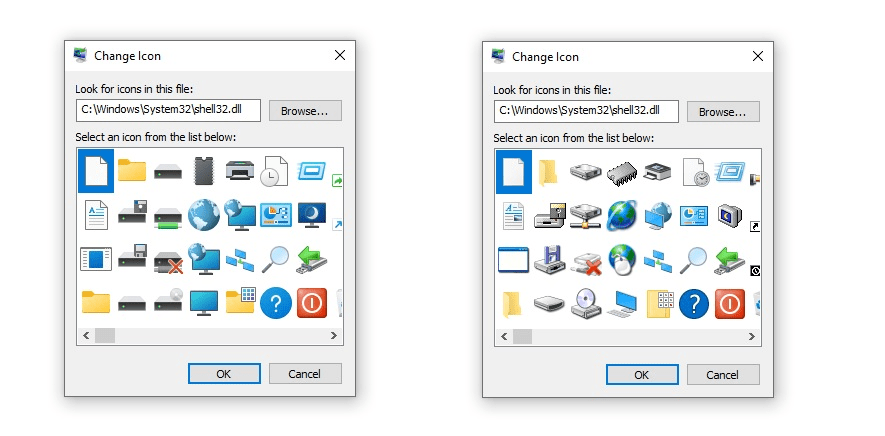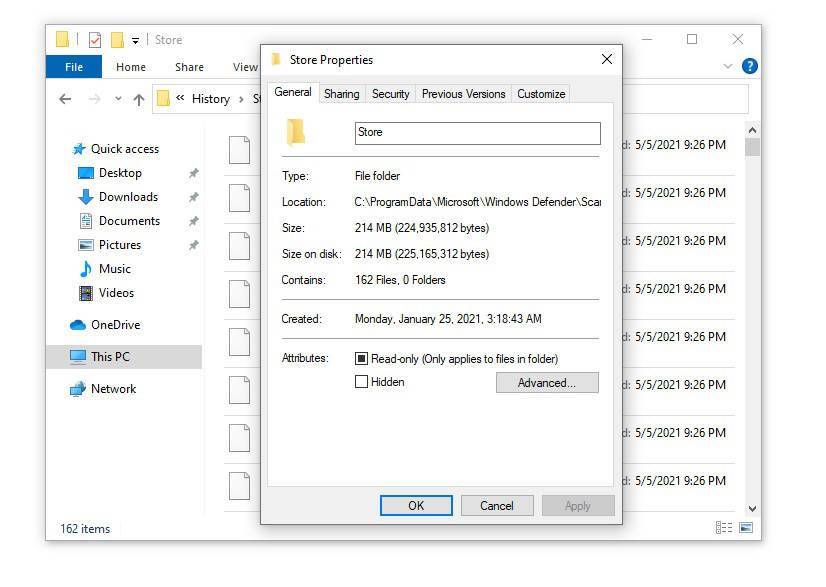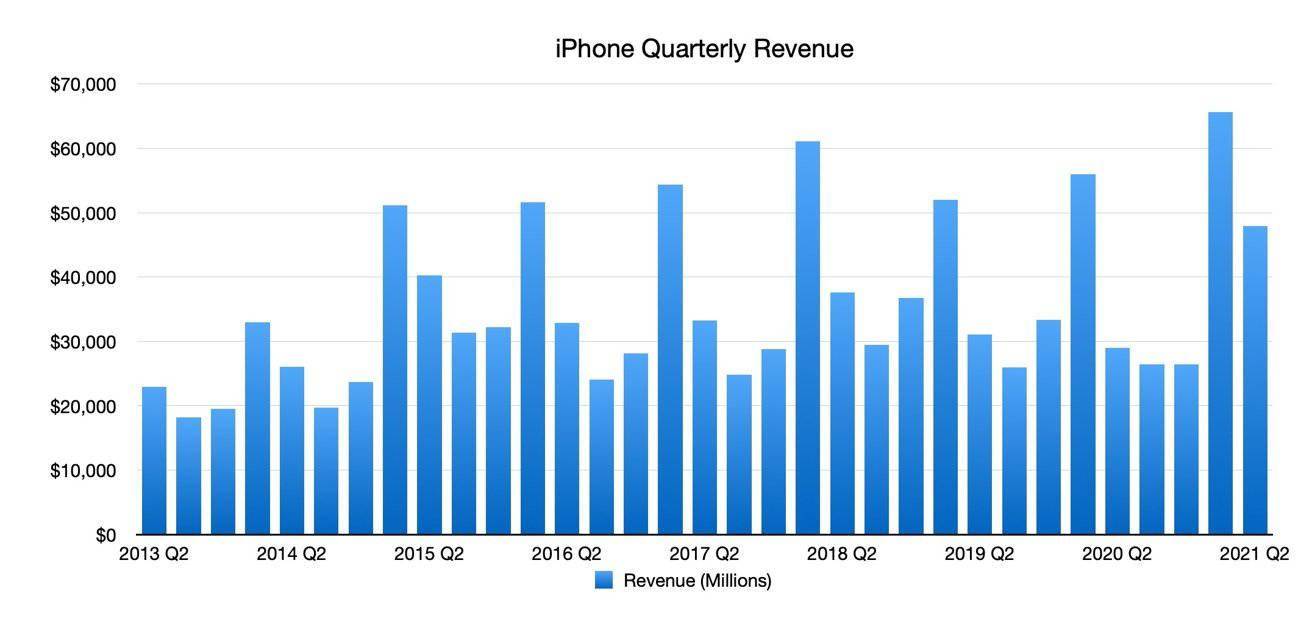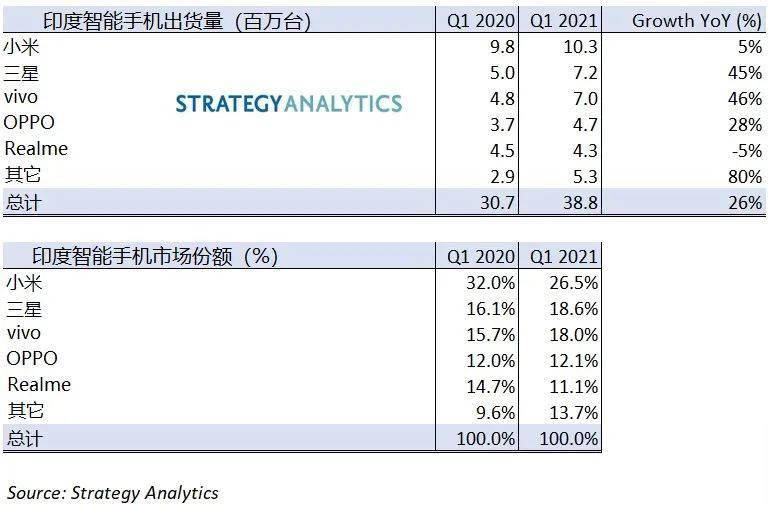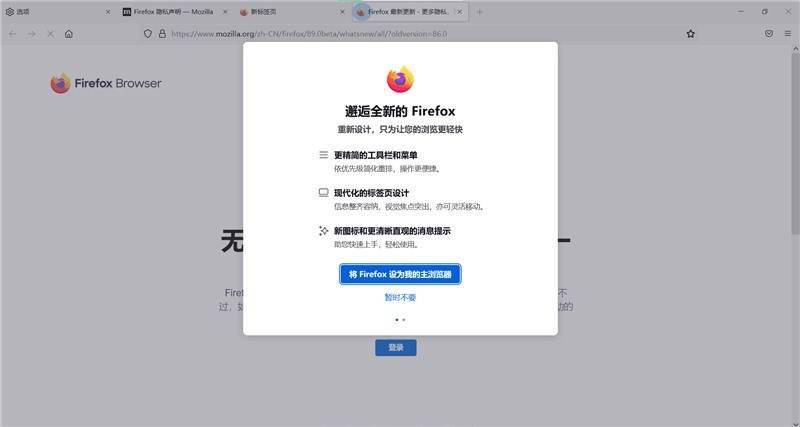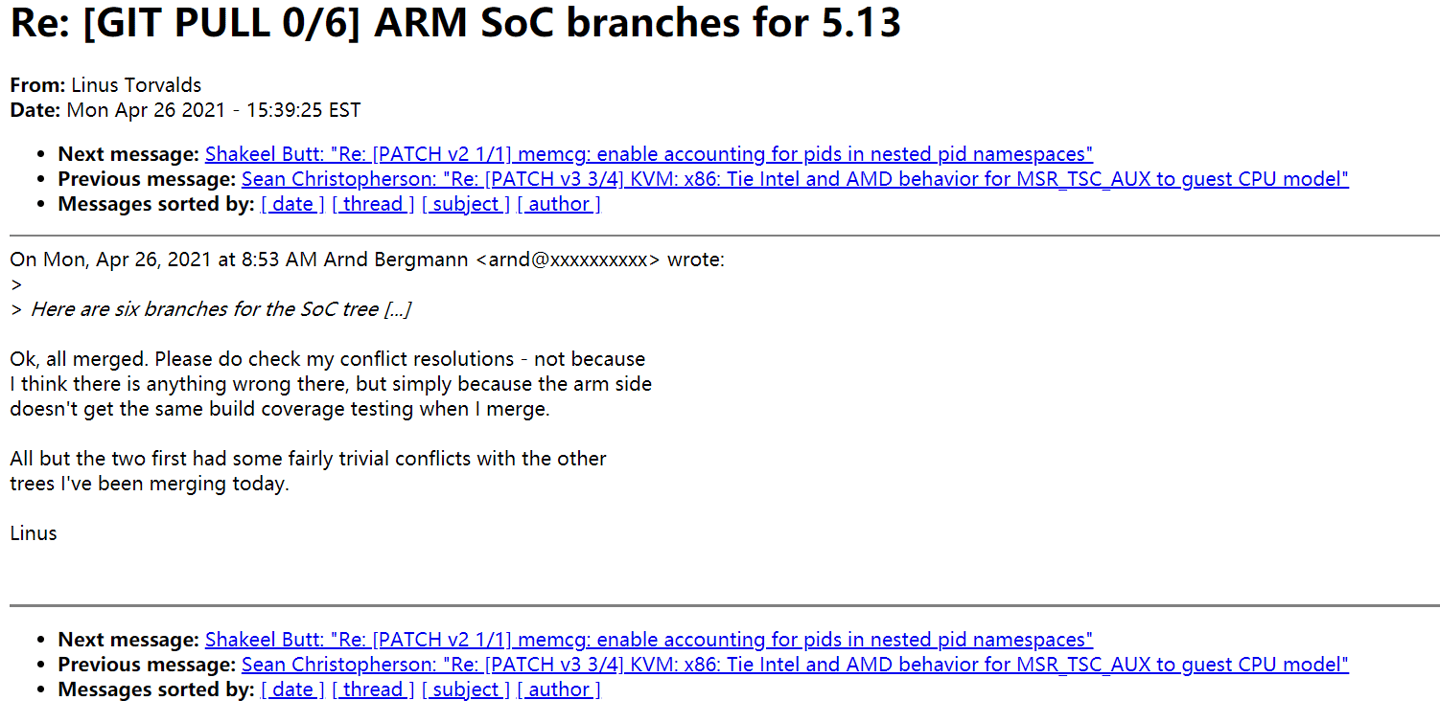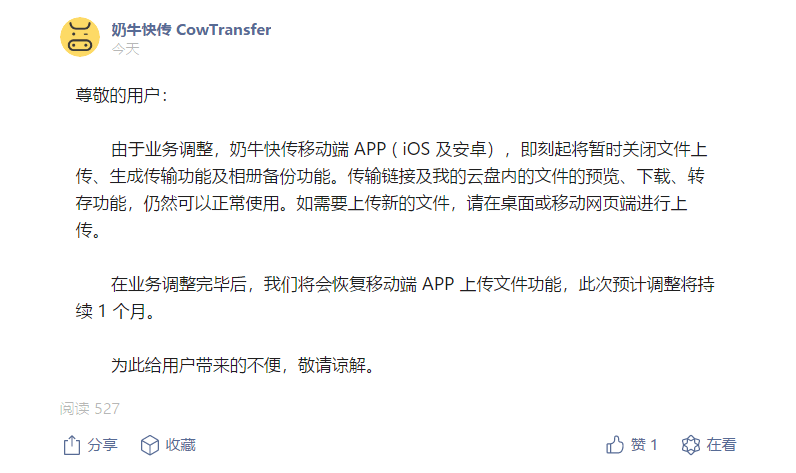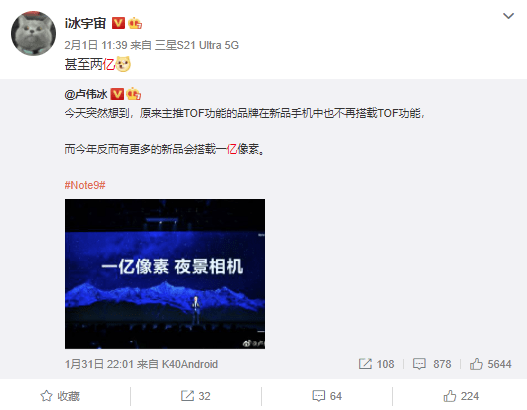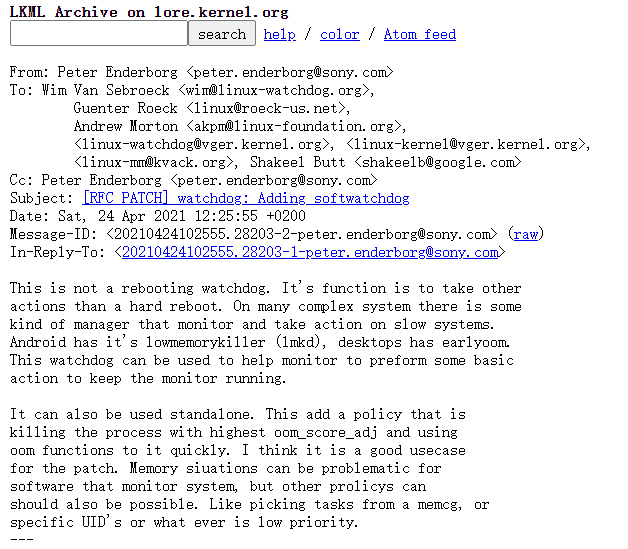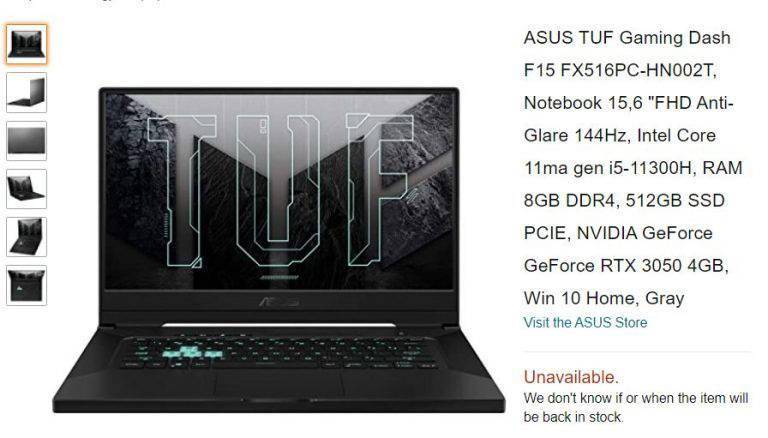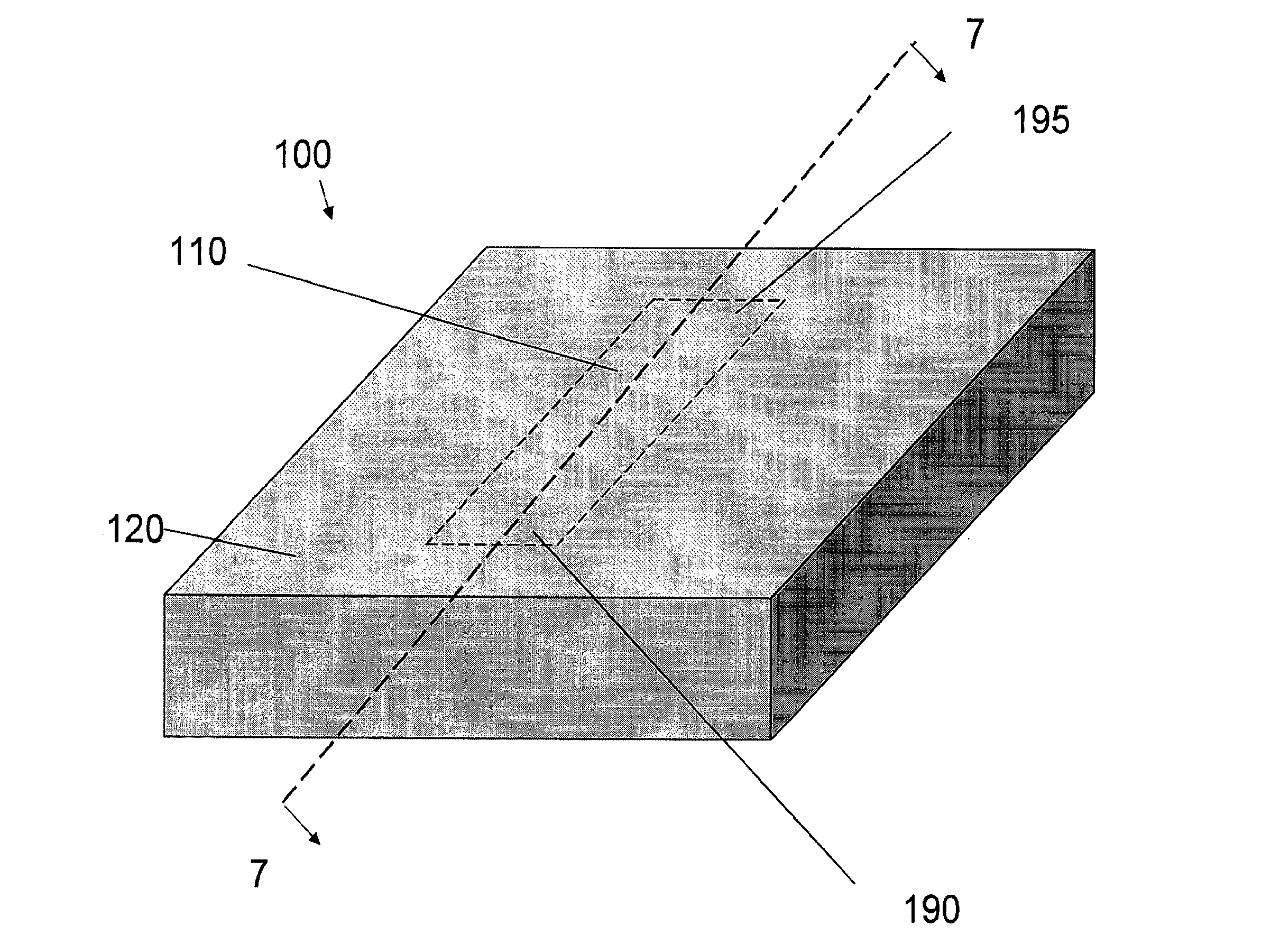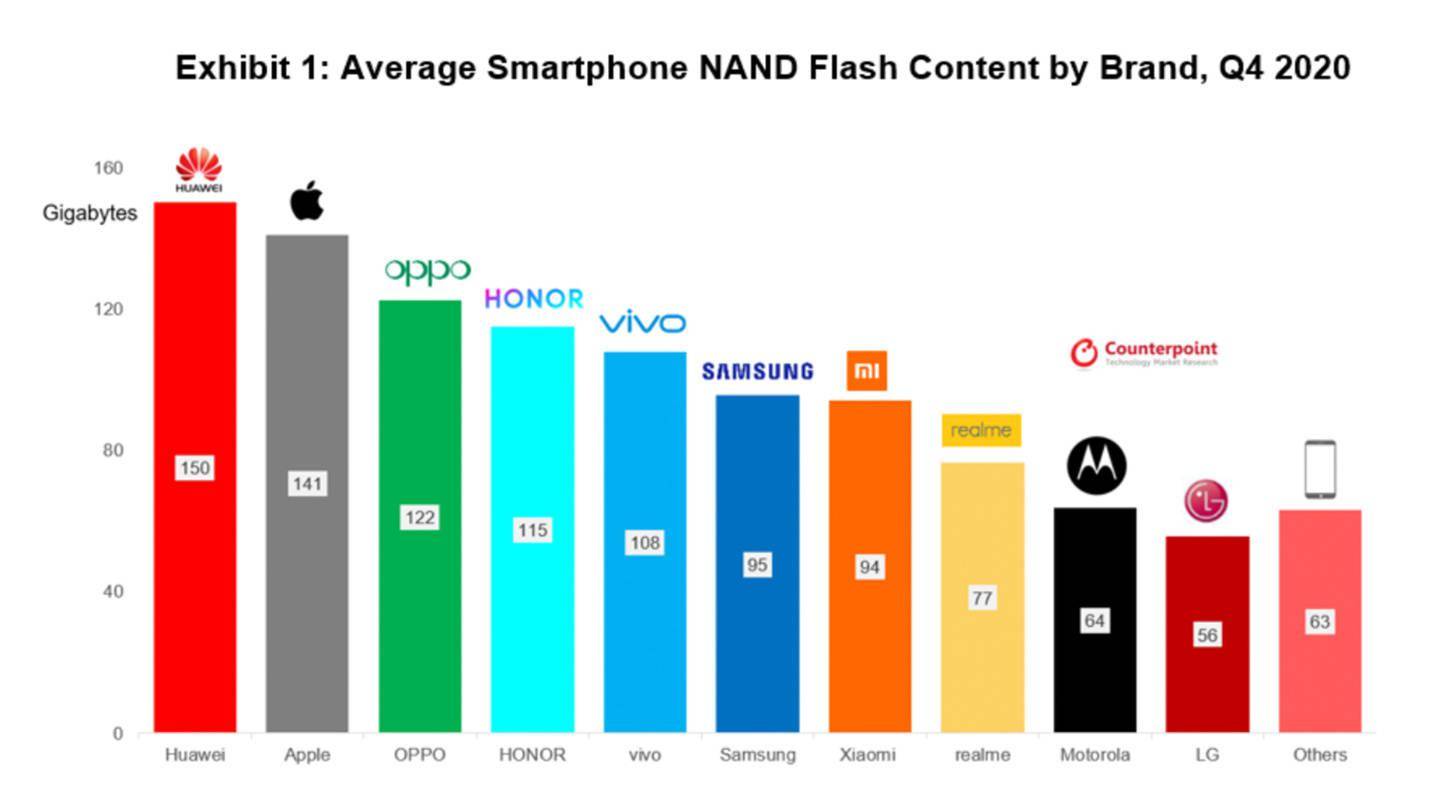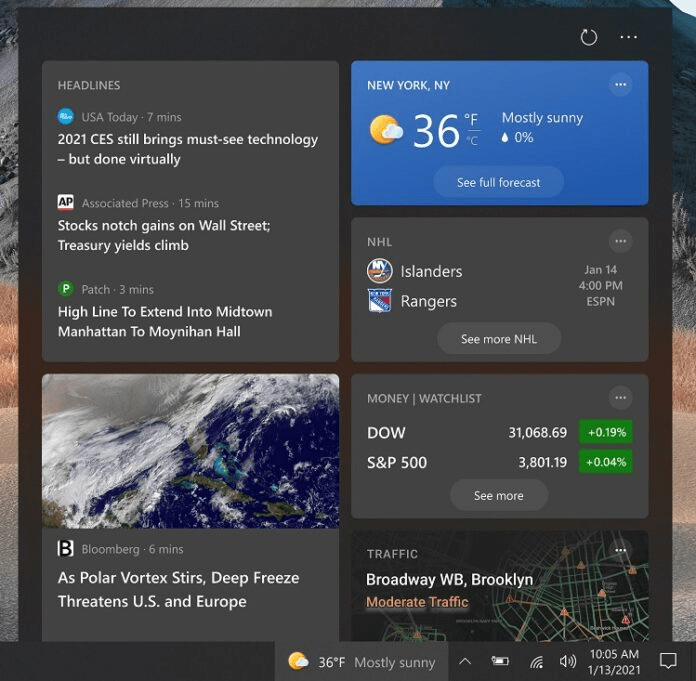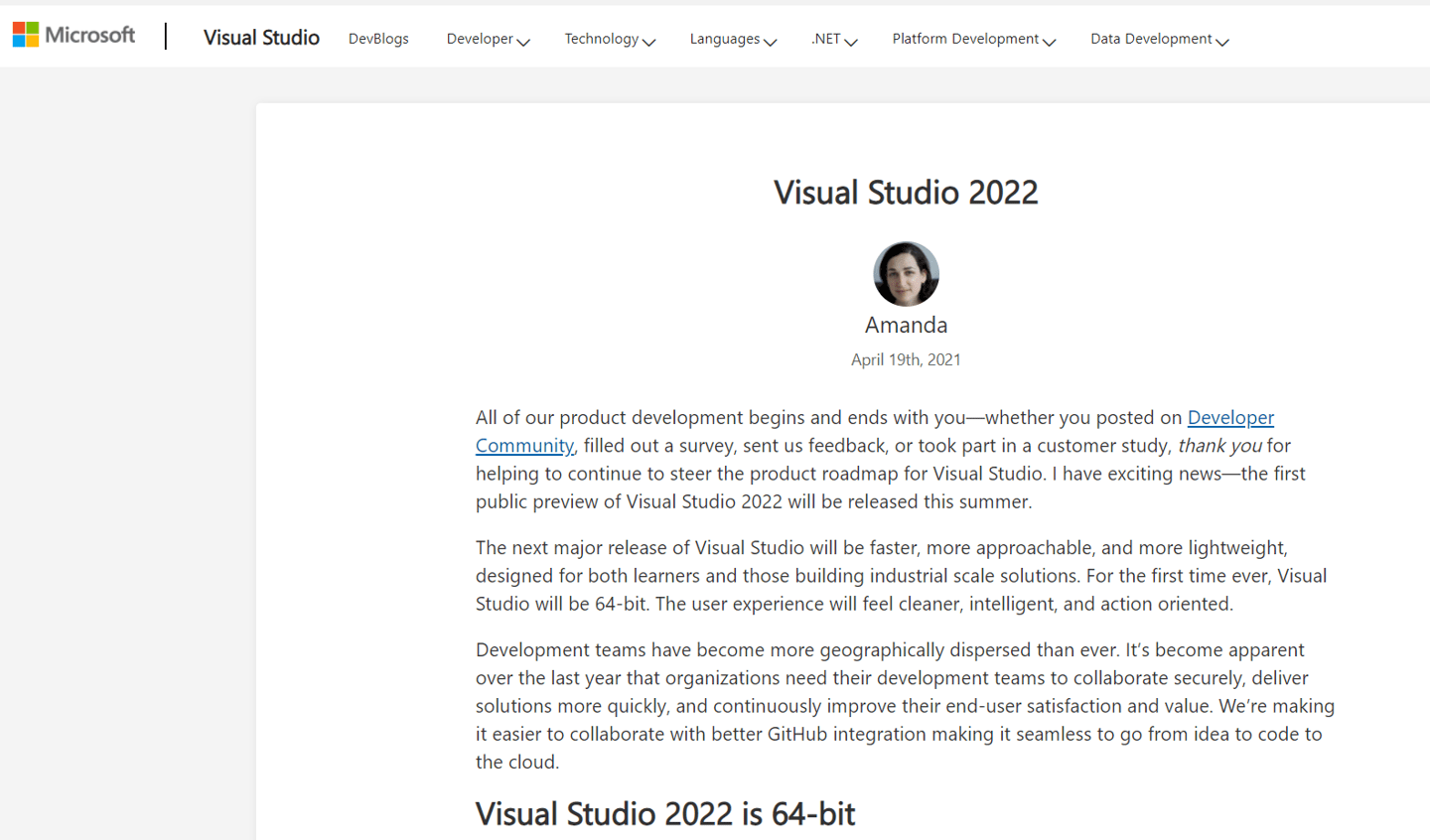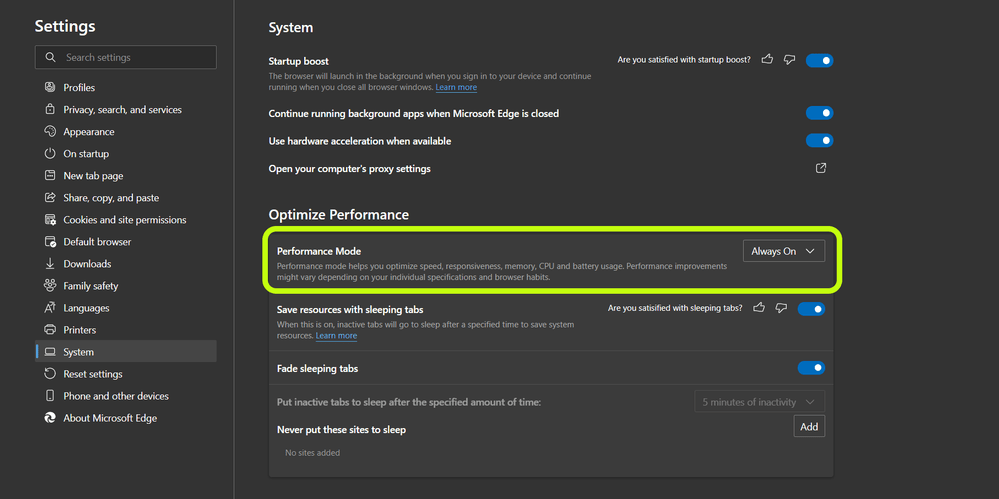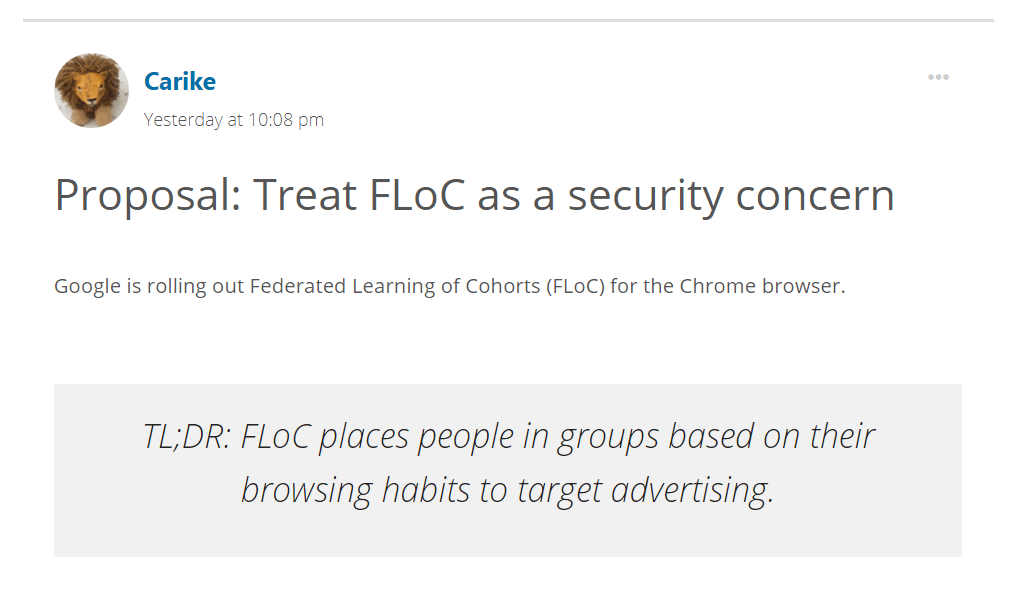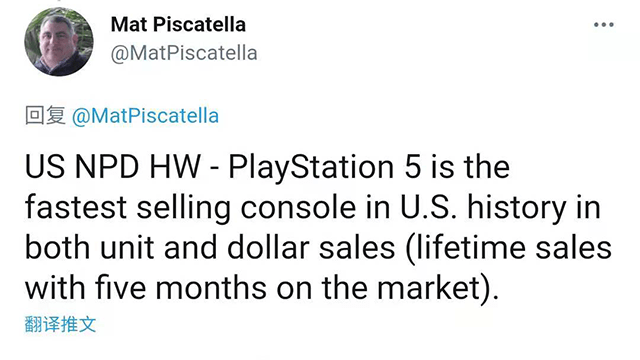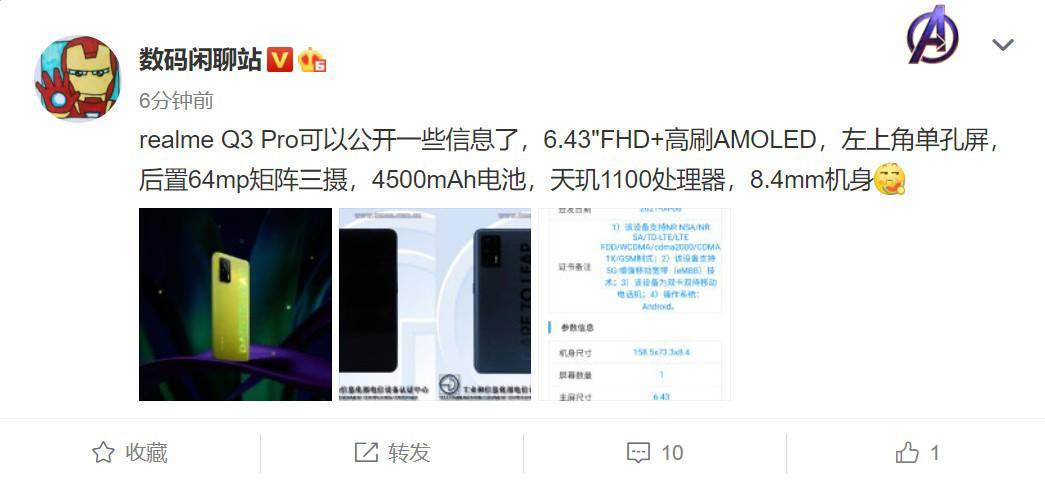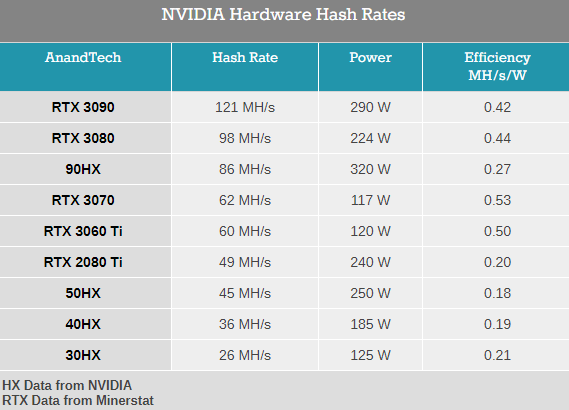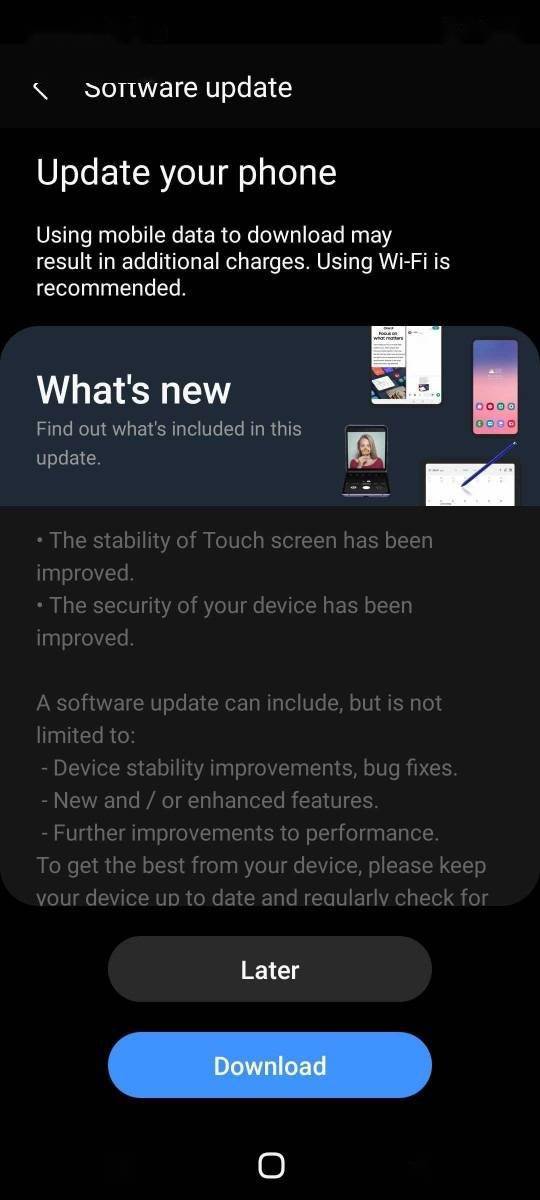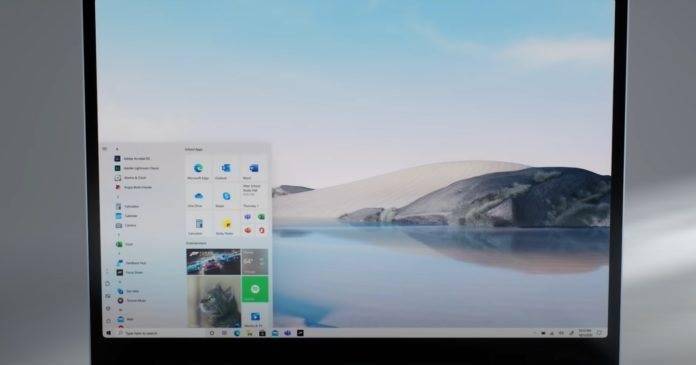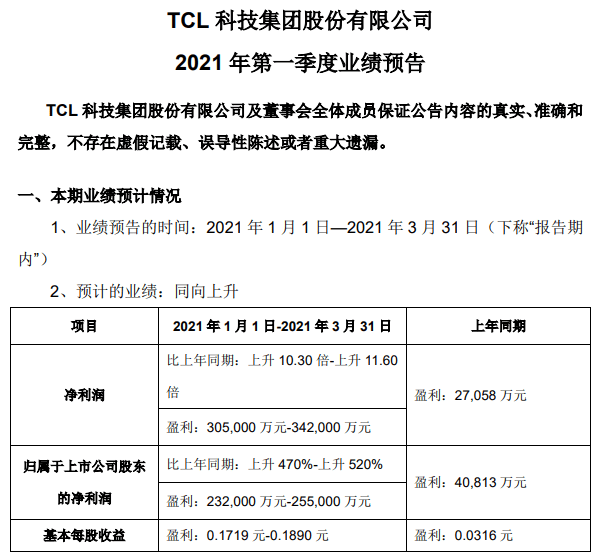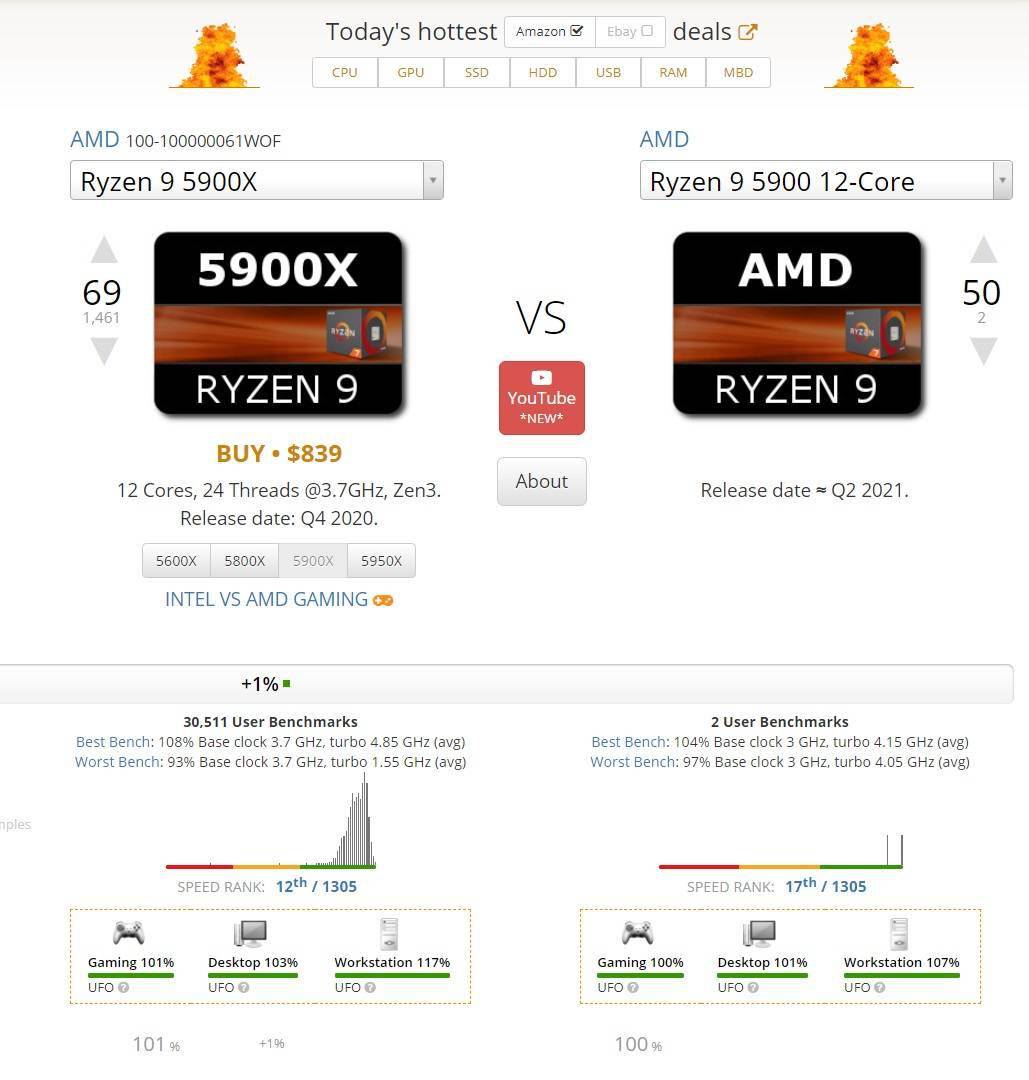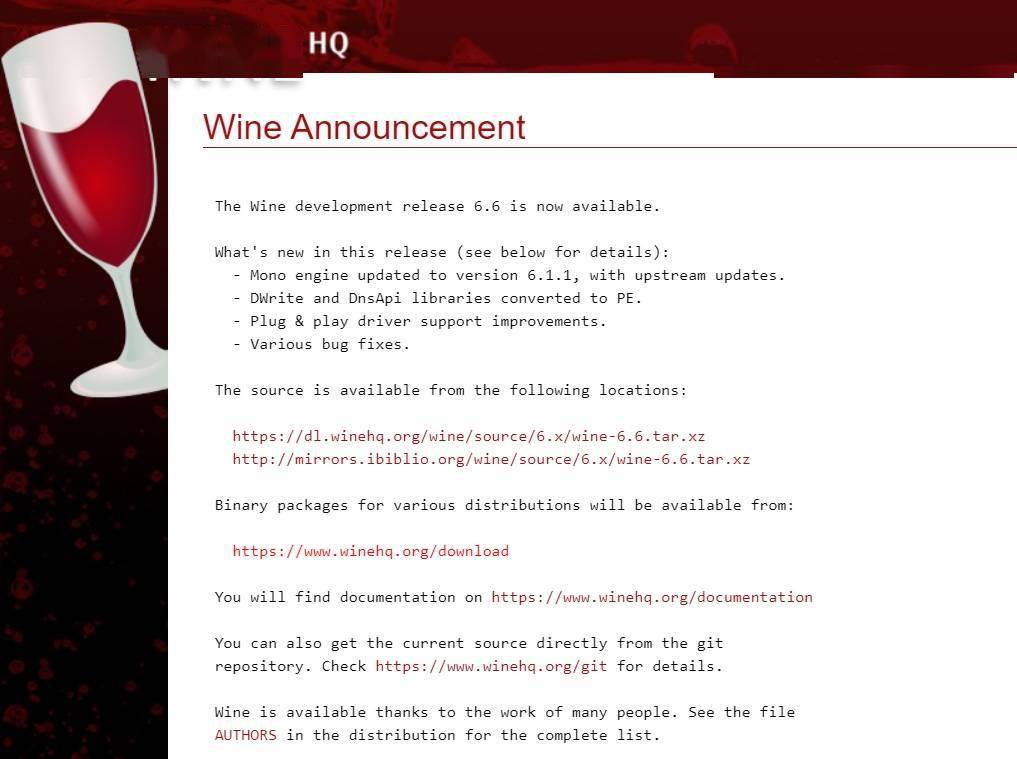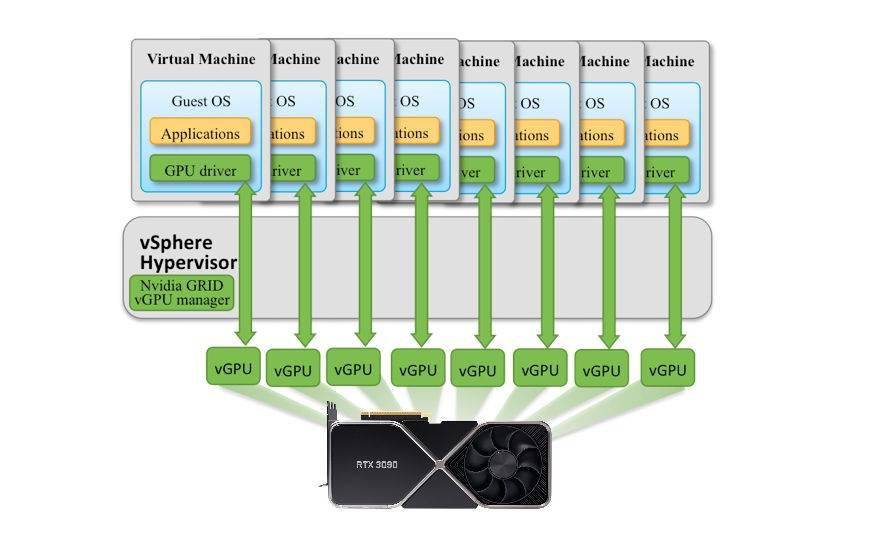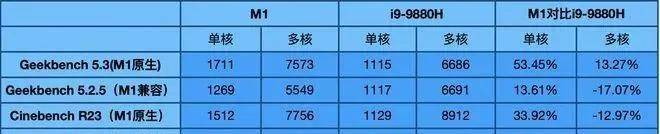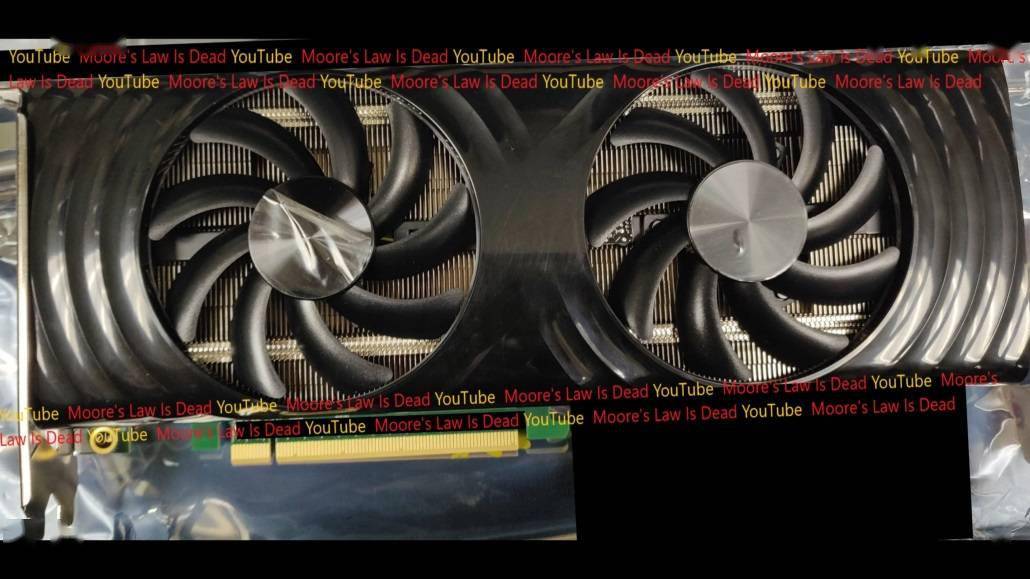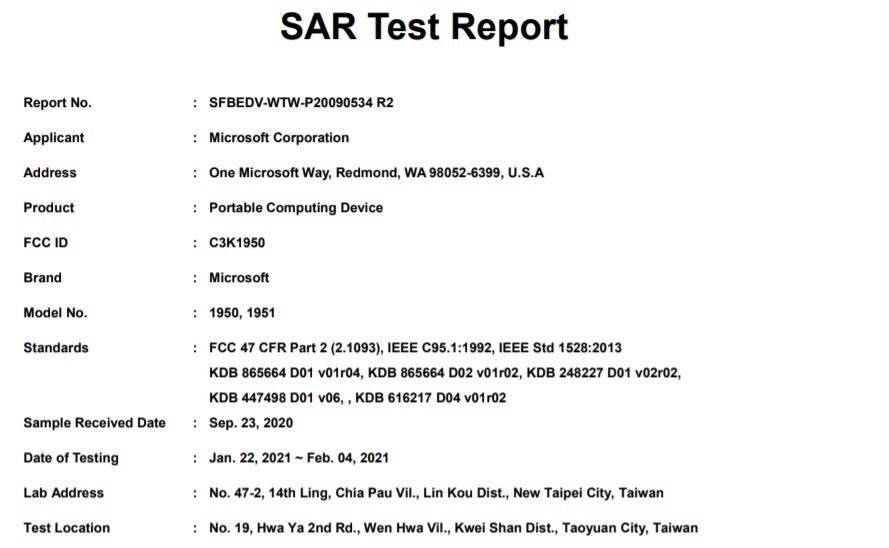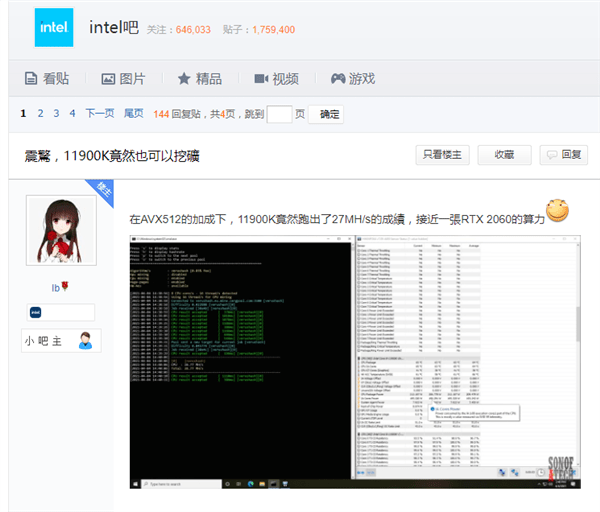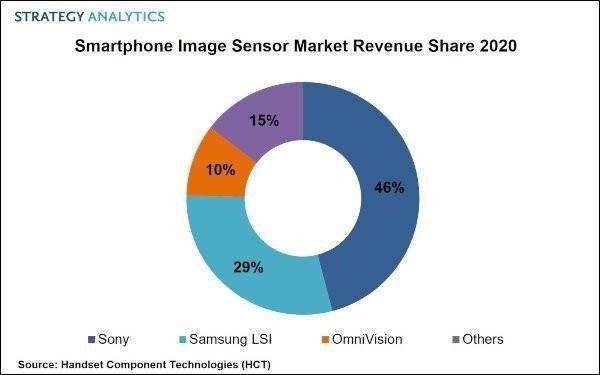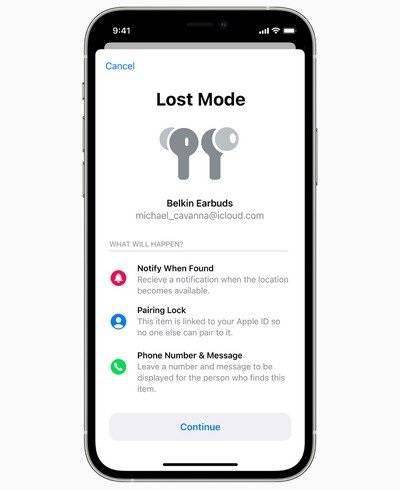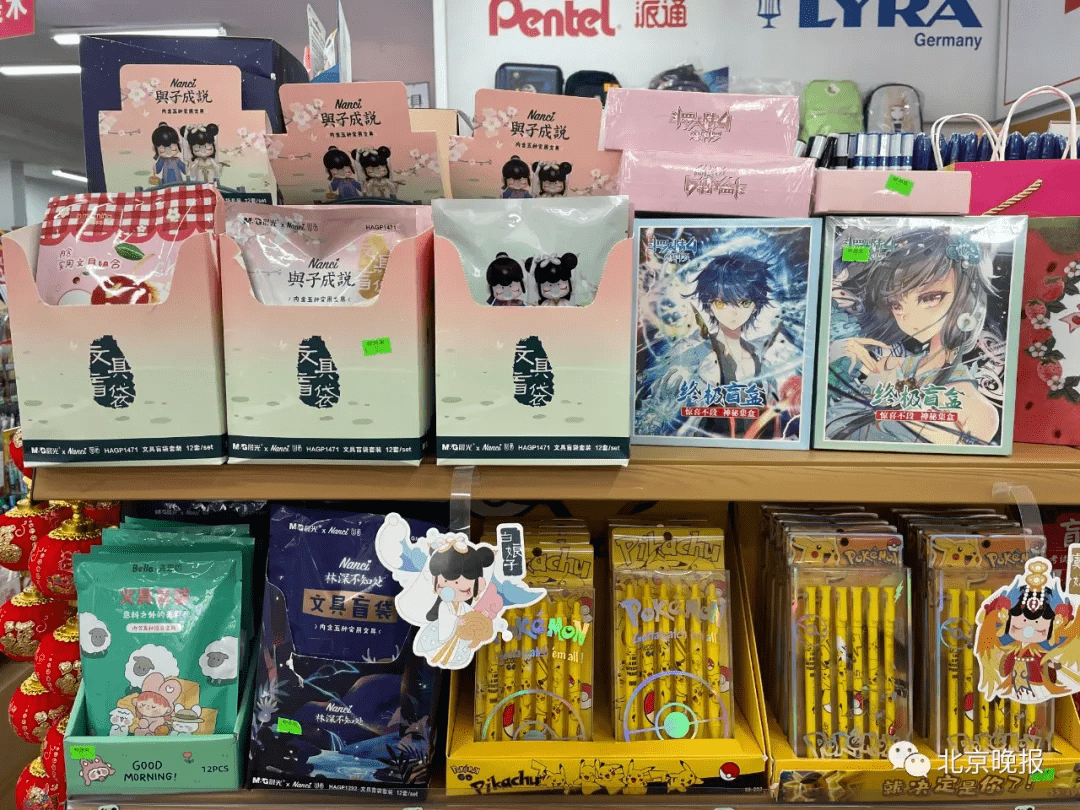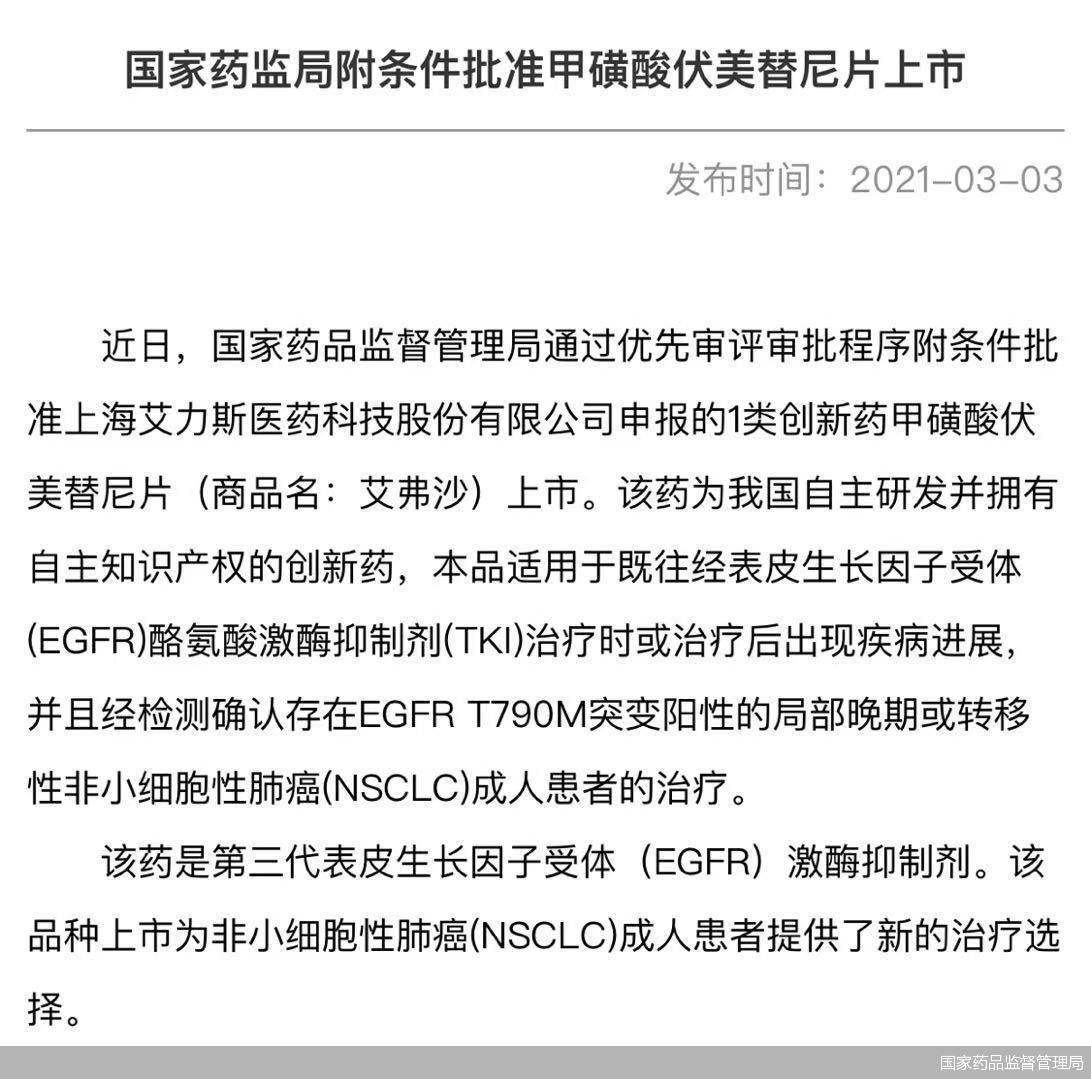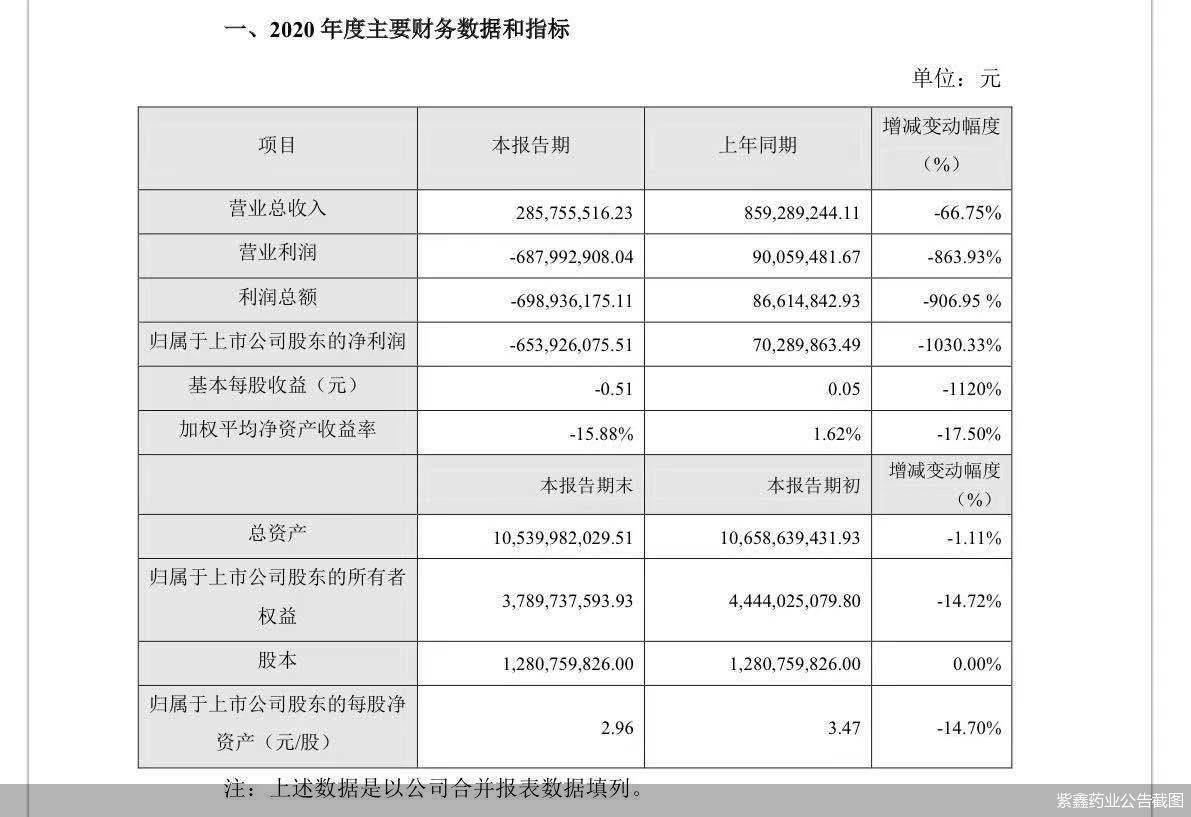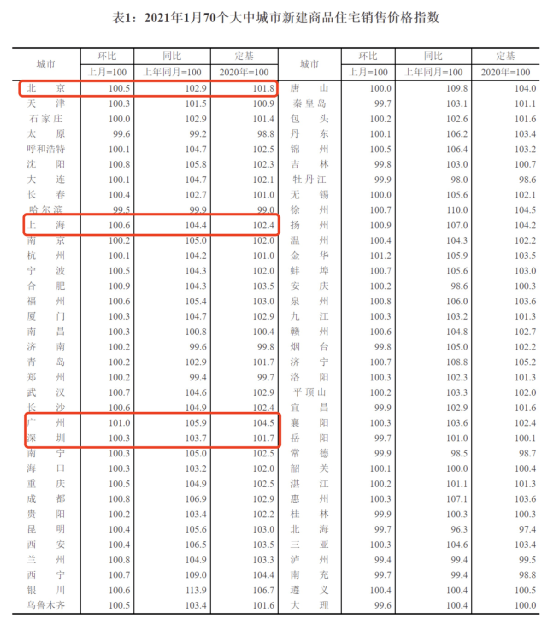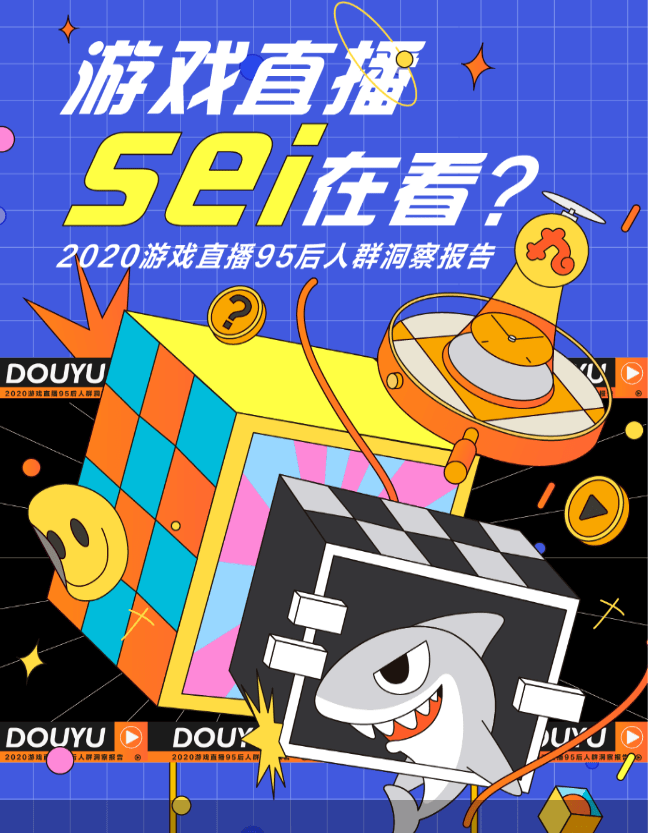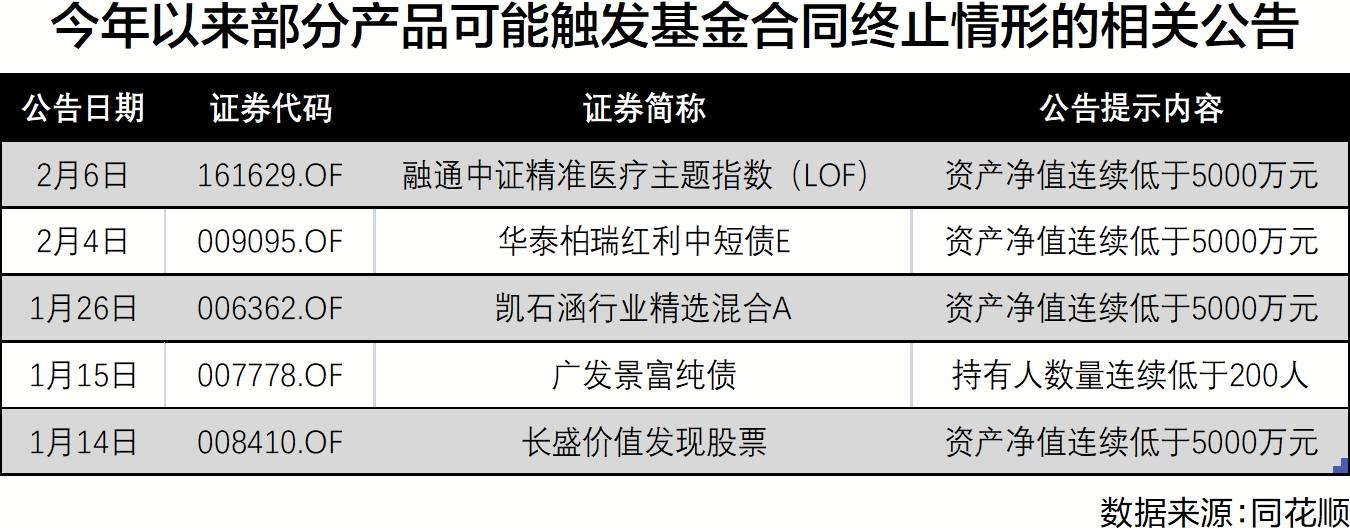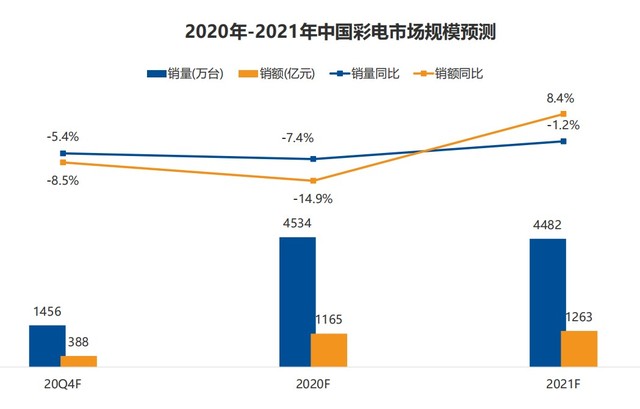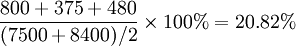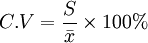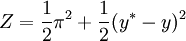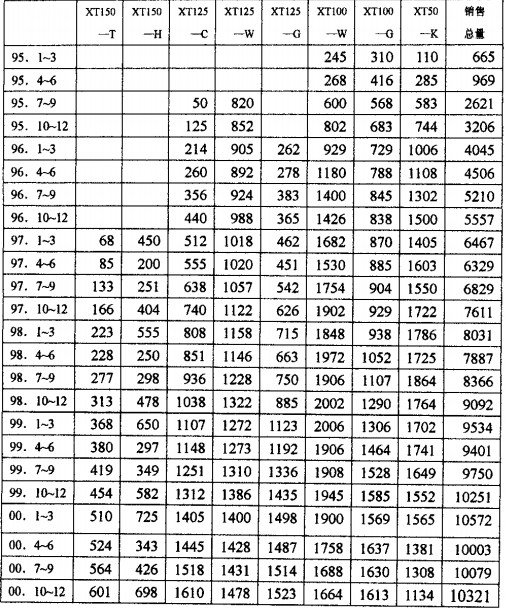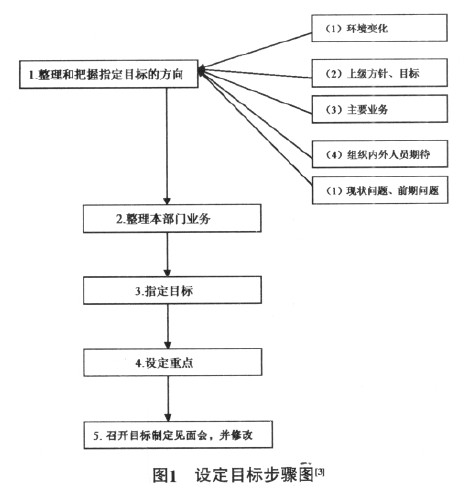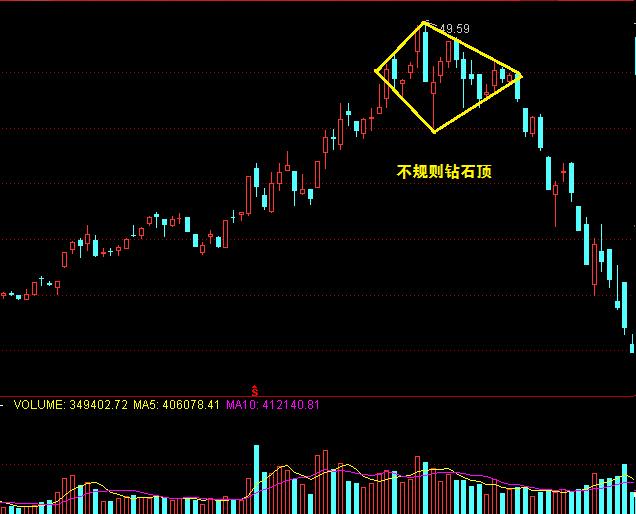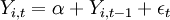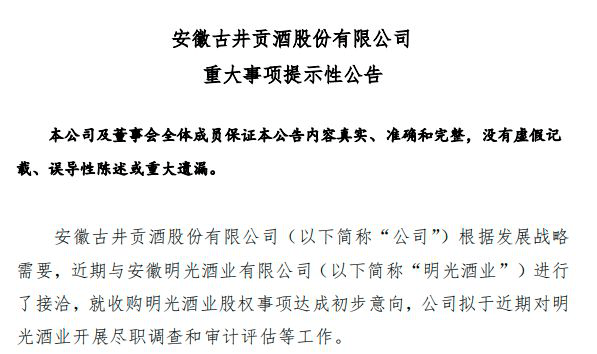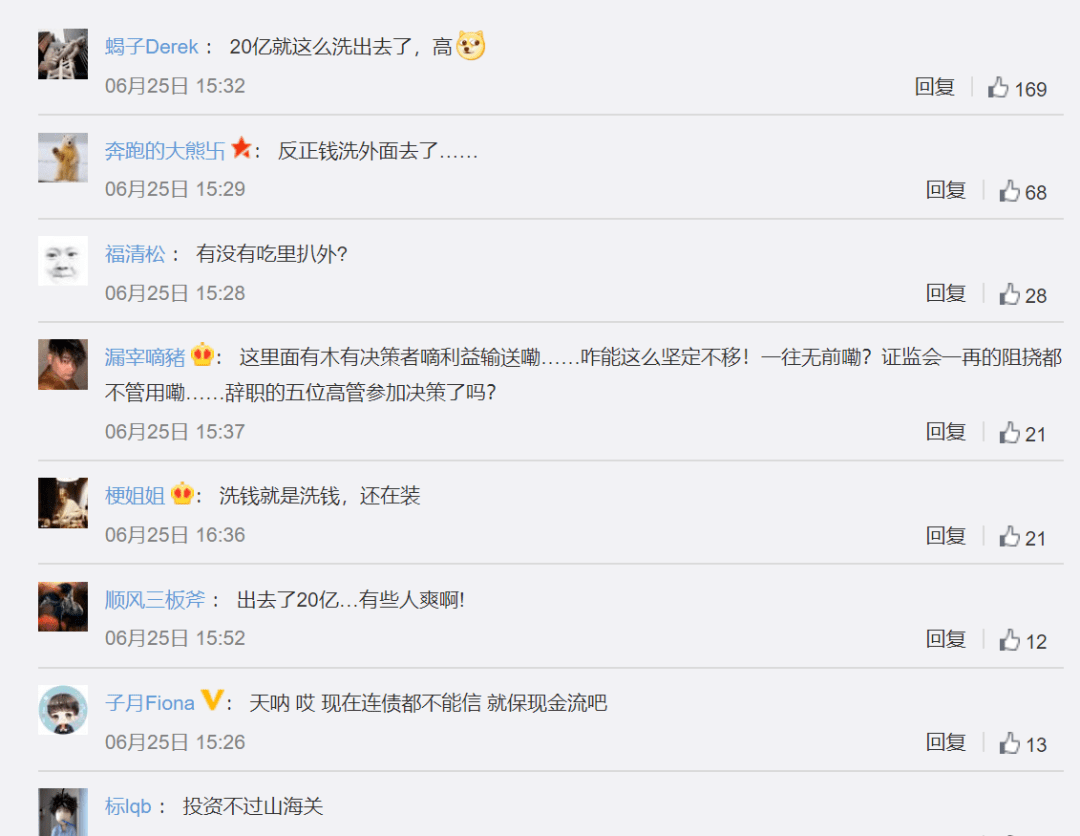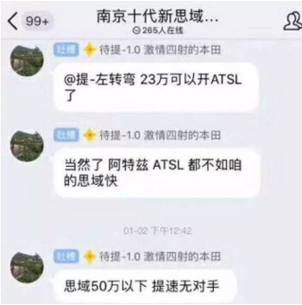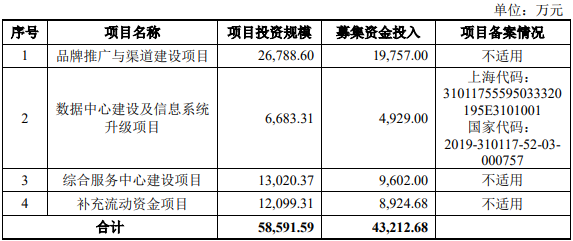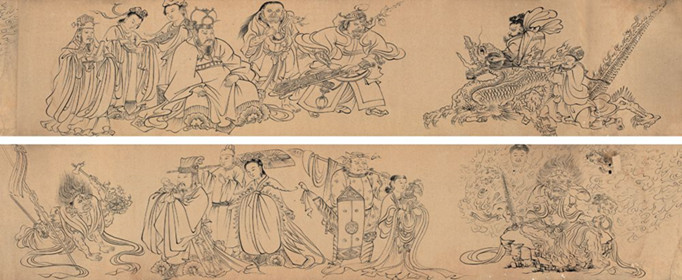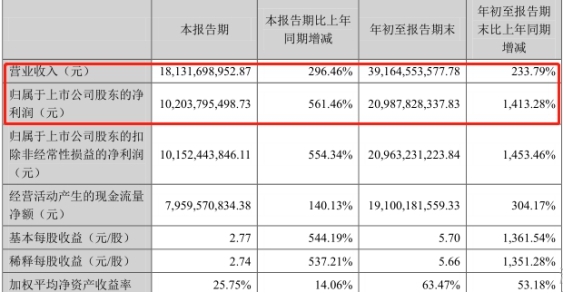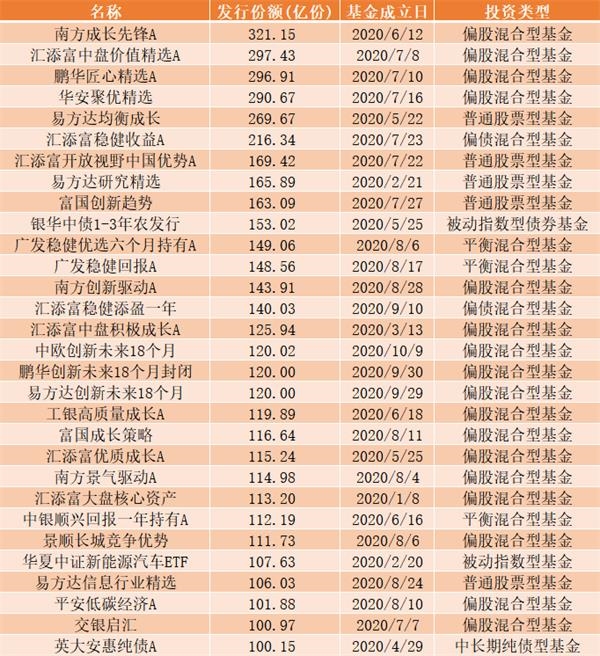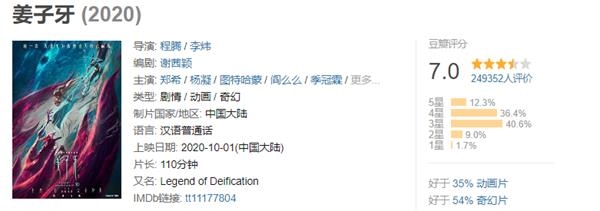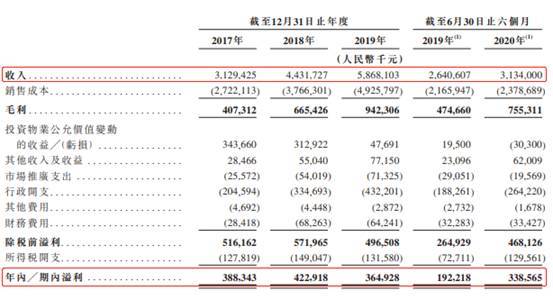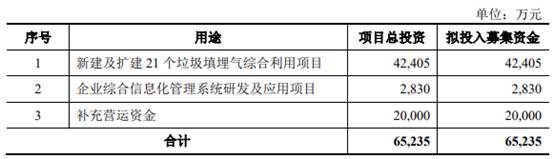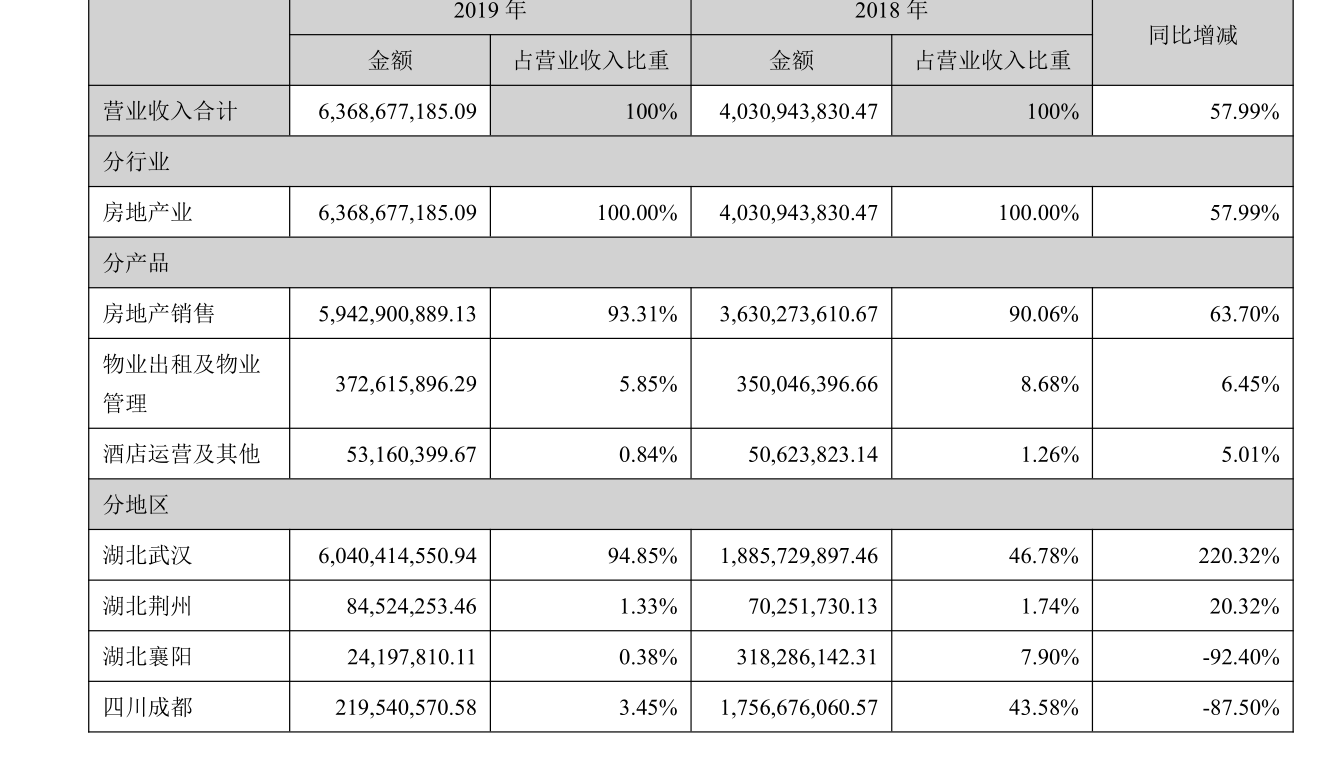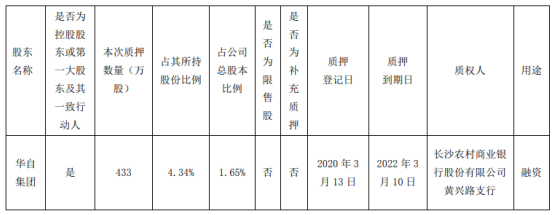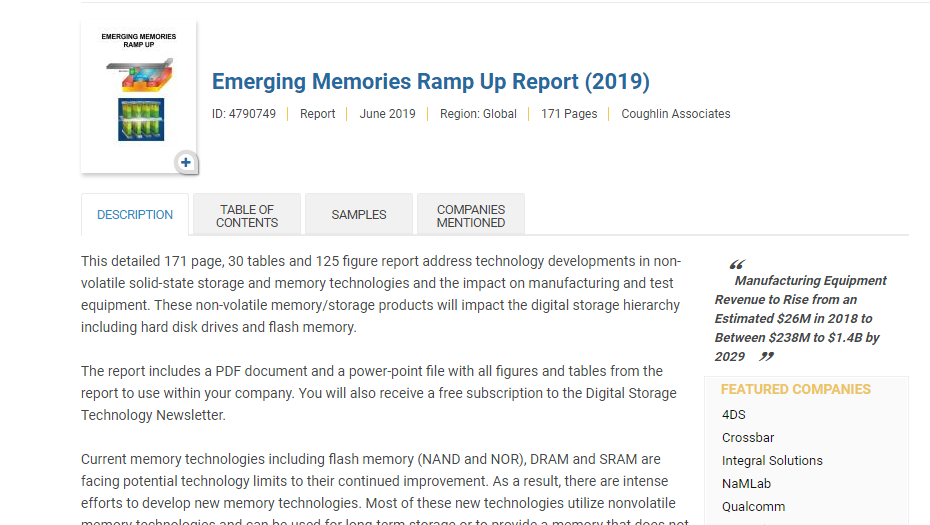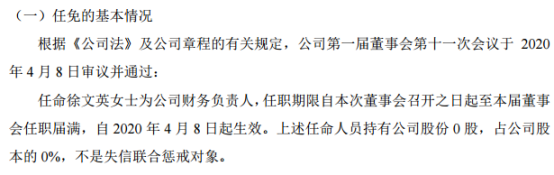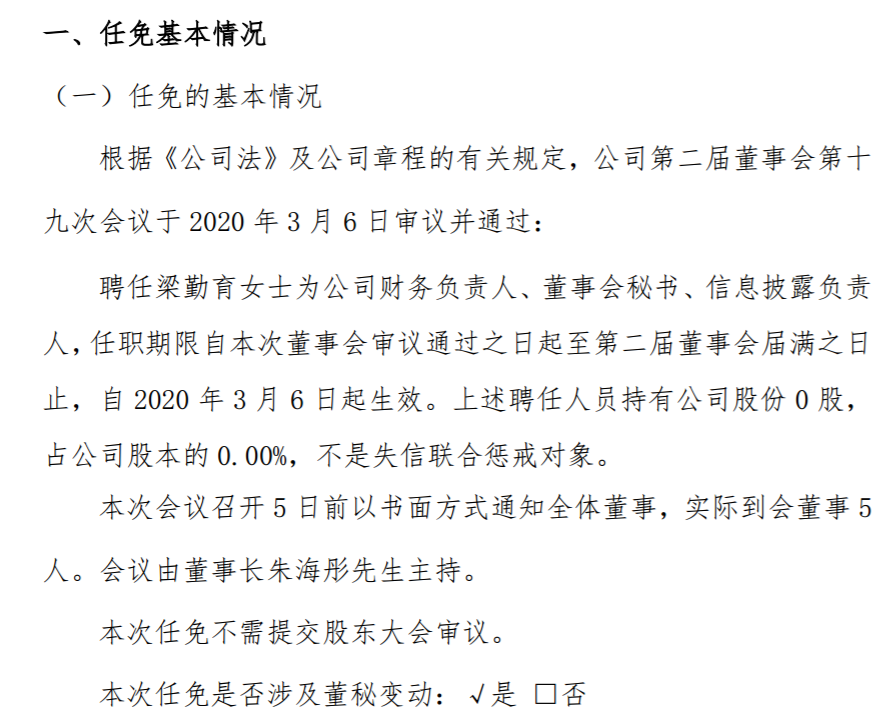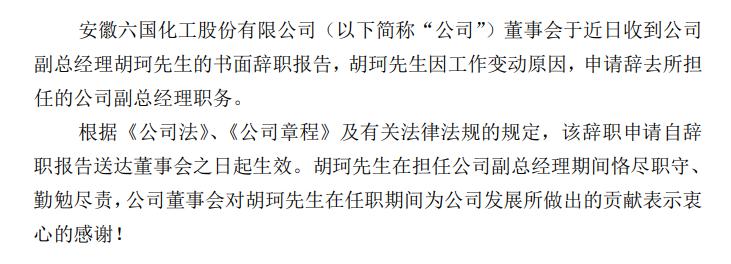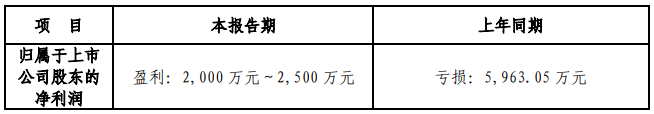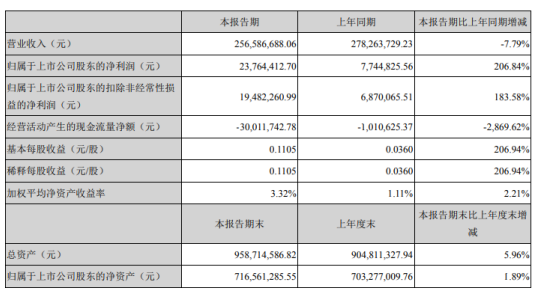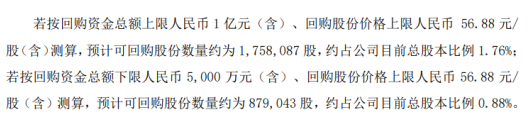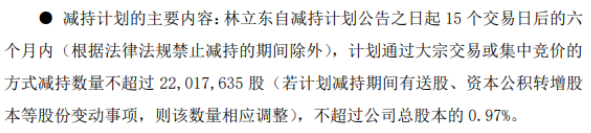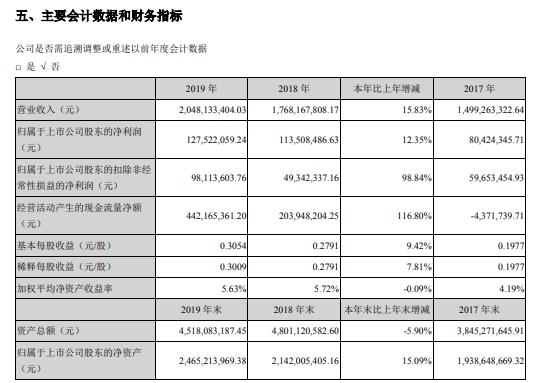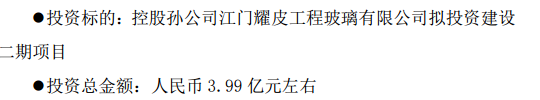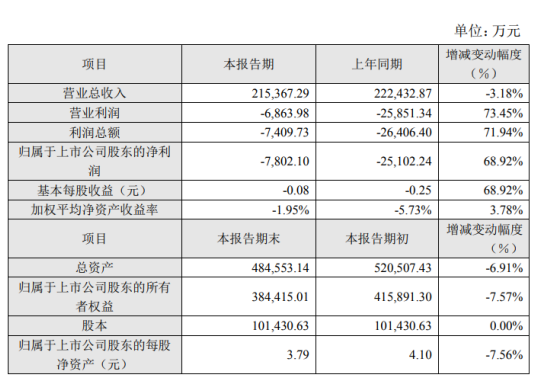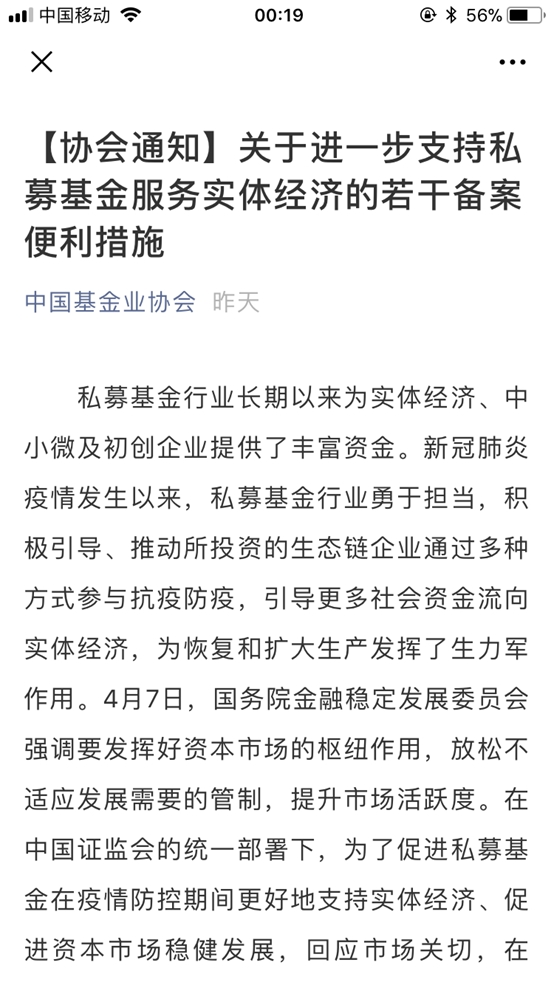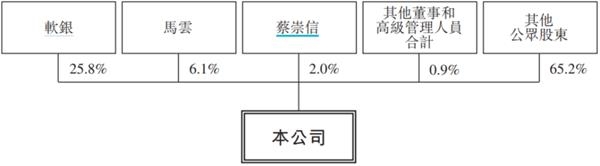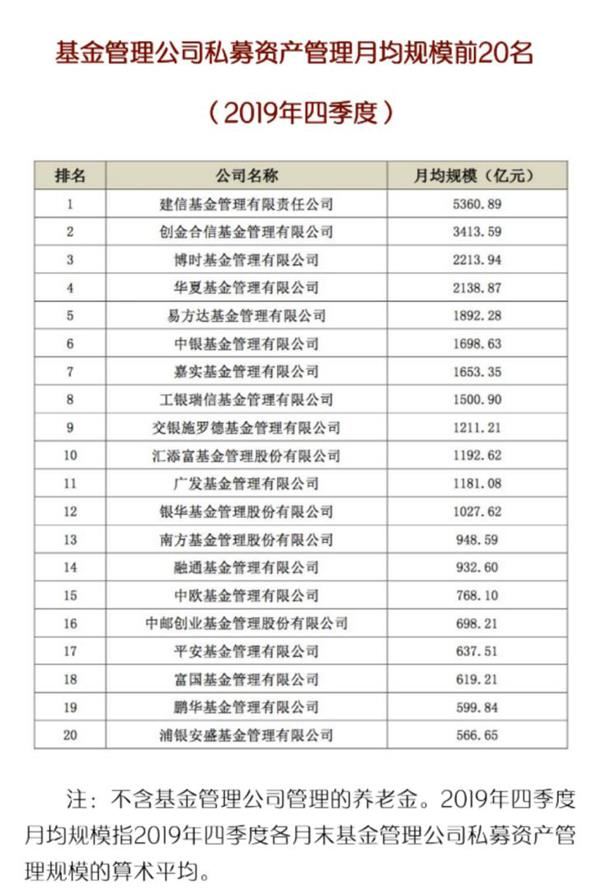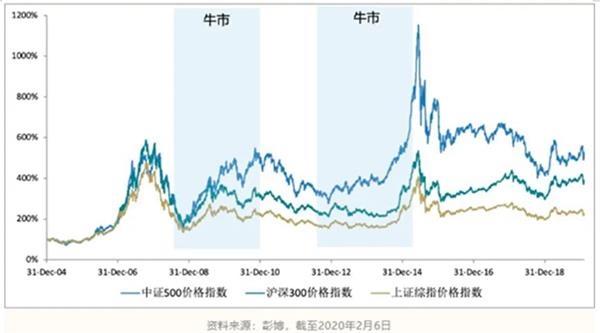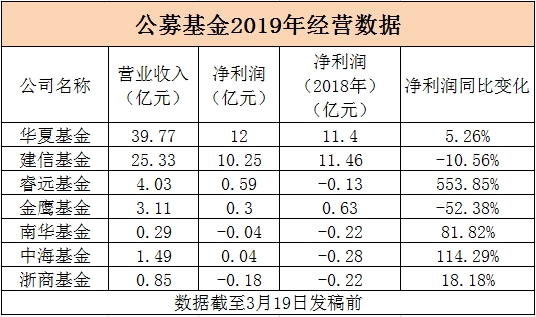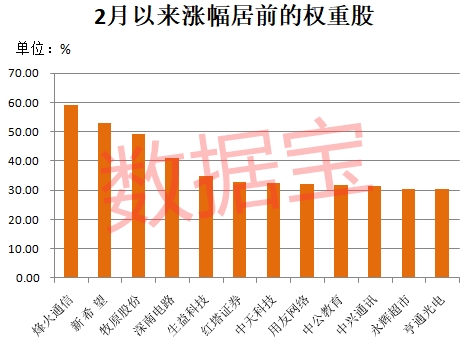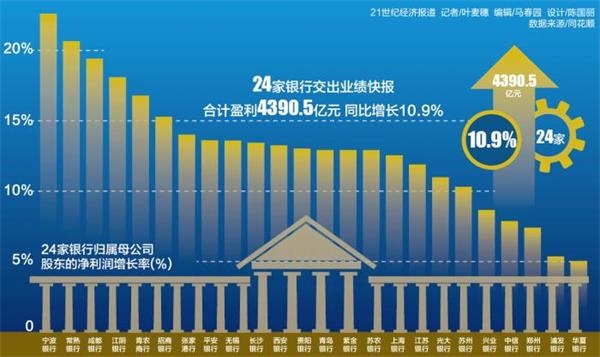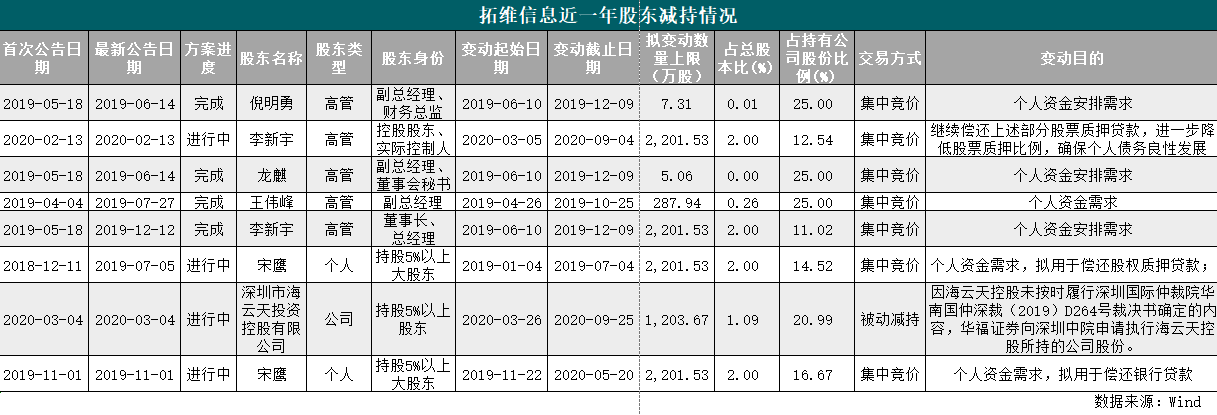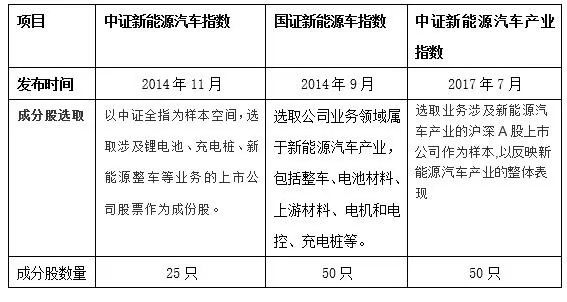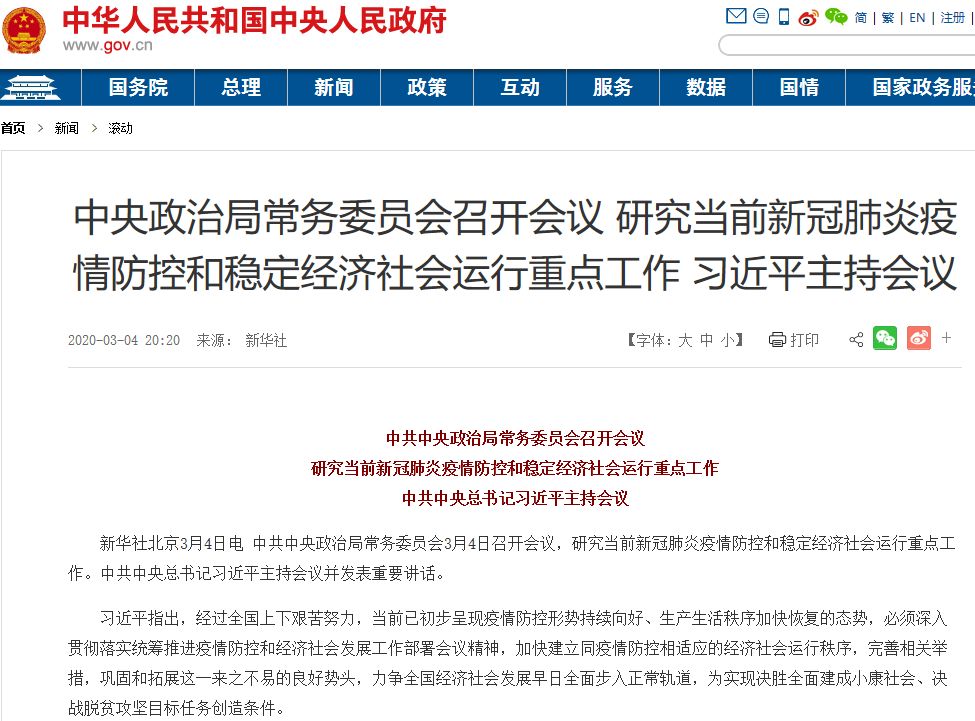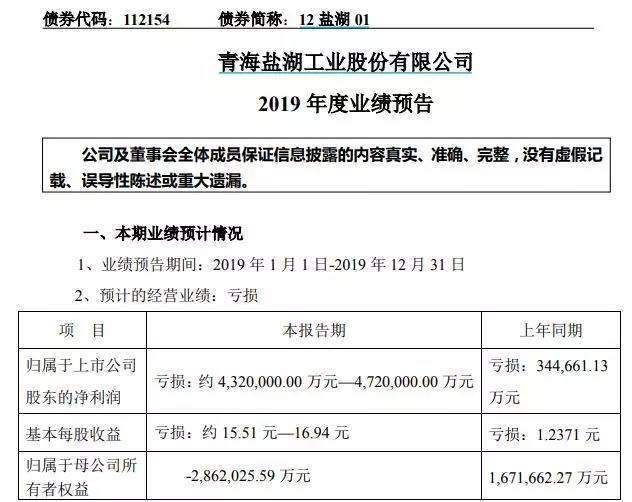近日,《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发布,追责体系重心由“行政处罚”转向“民事诉讼”,《纪要》同时对于中介责任做了明确划定。
专业人士表示,《纪要》的出台,是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明晰的一个历史关键时点,对于中介责任的划定更具时代意义。而中介责任的划定,对整个市场生态具有根本性影响,上述变化将给证券公司带来全方位的挑战。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中介机构法律责任加大,将促进其业务进一步规范开展。同时,对于业务激进的证券公司来说尤其不利,可能面临被淘汰出局的风险。而前置程序取消等系列维权,未来可能让证券公司疲于应诉。
而就《纪要》关于证券公司的责任豁免内容,有证券公司人士表示,相关条款应坚决执行,司法机构在判断证券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方面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
明确债券中介机构责任
“‘看门人’制度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治理方式之一,经过中介机构把关之后,相关主体即可进入证券市场。那么,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连带赔偿责任边界到底在哪儿?这是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一位资深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而边界这条线如何画,对整个市场的生态有根本性的影响。
“太左,券商可能不愿做业务,导致直接融资的债券市场活性丧失;太右,则约束不够,可能又会出现投资者利益没法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该人士表示,最高法此次划了一条合理的线,总的原则是过罚相当,是个辩证的平衡,在《纪要》当中以比较明确的方式确定下来。
《纪要》明确,债券中介机构依过错程度承担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连带责任,共涉及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纪要》规定了债券承销机构、债券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的核查把关责任,细化明确了债券承销机构的过错认定和免责抗辩细则,同时对债券服务机构的过错认定做了明确规定。
第二,受托管理人的赔偿责任。受托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损害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债券持有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三,债券发行增信机构与发行人的共同责任。监管文件中规定或者增信文件中约定增信机构的增信范围包括损失赔偿内容的,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要求增信机构对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而应负的赔偿责任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增信机构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发行人等侵权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第四,发行人与其他责任主体的连带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对其制作、出具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判断的,应当与发行人共同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五,为债券发行、上市提供服务的债券承销商、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债券服务机构,知道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者误导性陈述,仍然参与信息披露文件的制作或分发,或对相关事项出具肯定性意见的,应当与发行人共同对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打破刚性兑付以后,如果发行主体在债权到期时不能兑付,投资者就会找各种专业机构去算账。经济、信用下行期,特别是注册制推开以后,慢慢就会把民事责任各方的主体推到一个司法的轨道上来。”前述资深分析人士表示。
尽职调查临考
国泰君安相关人士认为,《纪要》对中介责任做出的明确界定,给券商提出了全方位挑战。
“《纪要》赋予了投资者大量的维权方式,特别是取消了债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处罚前置程序,未来可能让证券公司疲于应诉。”该相关人士表示,券商需要明确选择发行人的成本,适用更加严格、更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工作质量,进而有效降低债券违约事件的发生。未来证券公司会更加独立,所受到的监管兜底服务、政策服务、监管保护将逐渐减弱。
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陈健认为,在发债流程更规范、责任边界更明确的环境下,券商一方面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面临强化规范的市场环境。
“当意识到通过降低风控来应对竞争是一条死路时,券商会更加注重评估项目合规性,做好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通过质控合规来赢得更多投资者、市场、监管层的信任,以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陈健表示。
“券商面临的不仅是业务承接工作量的加剧,也面临如何确保其他中介服务商工作质量的问题。”海通证券债券融资总部总经理李一峰如是总结。
针对承销商尽职调查工作,《纪要》将“不适当地省略工作计划中规定的步骤”作为确定承销商过错的标准之一,并在第29条免责抗辩中详细罗列了尽职调查的各个步骤。由此,承销商在尽职调查上投入的工作量和分配的精力都亟待提升,否则将面临最终被追责的后果。
“由此看来,《纪要》对于现有市场中承销商尽职调查工作的开展无疑是一次规范化的洗涤,也是对现有市场中承销商机构进行的一次正面筛选,对于市场中介机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重要时机。”李一峰强调。
“按照《纪要》要求,承销商不能再简单依赖于其他债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而需要自行进行核查,甚至是调查和复核。在此种要求之下,如果其他债券服务机构工作质量不高,将直接导致承销商工作量加大,也加大承销商最终承担责任的风险。”李一峰进一步分析称,由此,在业务承接过程中,承销商应当适当关注具体业务其他中介服务商的配备和质量,尽量确保尽职调查工作量投入可控,以及最终风险可控。
“承销一只债券会有多大的风险敞口?不用证监会每天盯着喊着加强内控,机构自己就能算出来可能面临多大的风险。”前述资深人士表示,券商在做内控的时候有一个可预期性。
“行政”转“民事”影响可预见
“追责体系理论上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以前行政一条腿独大,民事几乎没有,刑事也很少。”前述资深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追责重心向民事诉讼转移后,包括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直接面对的不再是证监会,而是所有的投资者和全国各地的法院。
李一峰认为,《纪要》第9条明确持券人和投资人以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起诉要求发行人等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时,无需有生效的行政处罚或者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前提要件,是《纪要》将追责重心从“行政处罚”转向“民事追责”的一大体现。
“《纪要》增加了持券人要求管理人进行积极起诉的依据和筹码,债券管理人在处理债券违约纠纷上的工作投入需要增加。这个投入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长期发展是有益的。同时,明确券商等债券管理人可以自身信誉提供担保,减小了持券人维权成本,也加大了券商的信誉风险。”李一峰表示,然而,对作为债券管理人的证券公司等机构而言,债券管理人本身仅是中介机构,而非最终权利人,是否以自身信誉为持券人追索做保,以及该等担保是否应该收获相应对价,也是各大券商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述国泰君安相关人士强调,追责体系重心的变化,对证券公司无疑会产生诸多影响,对于业务寂静公司尤其不利。
其一,《纪要》的发布提高了投资者的参与权,加大了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力度。证券公司未来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要更加真实透明,经办人员要树立严格的合法合规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意识,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证券公司内部风险识别的专业能力。
其二,这种转变对于业务激进的证券公司来说不利。此类证券公司可能因为民事索赔导致其未来债券业务风险敞口、风险准备金计提增加,进而导致其相应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甚至面临被淘汰出局的风险。
“当然,守法合规经营的证券公司有可能在将来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具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该相关人士补充道,为应对《纪要》提出的挑战,证券公司应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建立证券公司内部评级体系,确保承销债券的质量。同时,债券市场需要多方维护,包括证券公司、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在整个债券发行合作过程中能各司其职,在债券风险识别方面提供专业、有底线的服务。
“《纪要》关于证券公司的责任豁免条款必须坚决执行,司法机构在判断证券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情况,不能‘唯结果论’和‘唯维稳论’”。上述相关人士同时提醒,以尽职调查为例,如果发行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主观上存在故意隐瞒,证券公司可能穷尽了所有调查手段也无法获取全面真实的信息,譬如现实过程中,发行人存在违规担保、隐瞒重大案件,甚至一些商业银行出具的函证回复也存在虚假表述,在这些情形下,推定证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将有失偏颇。